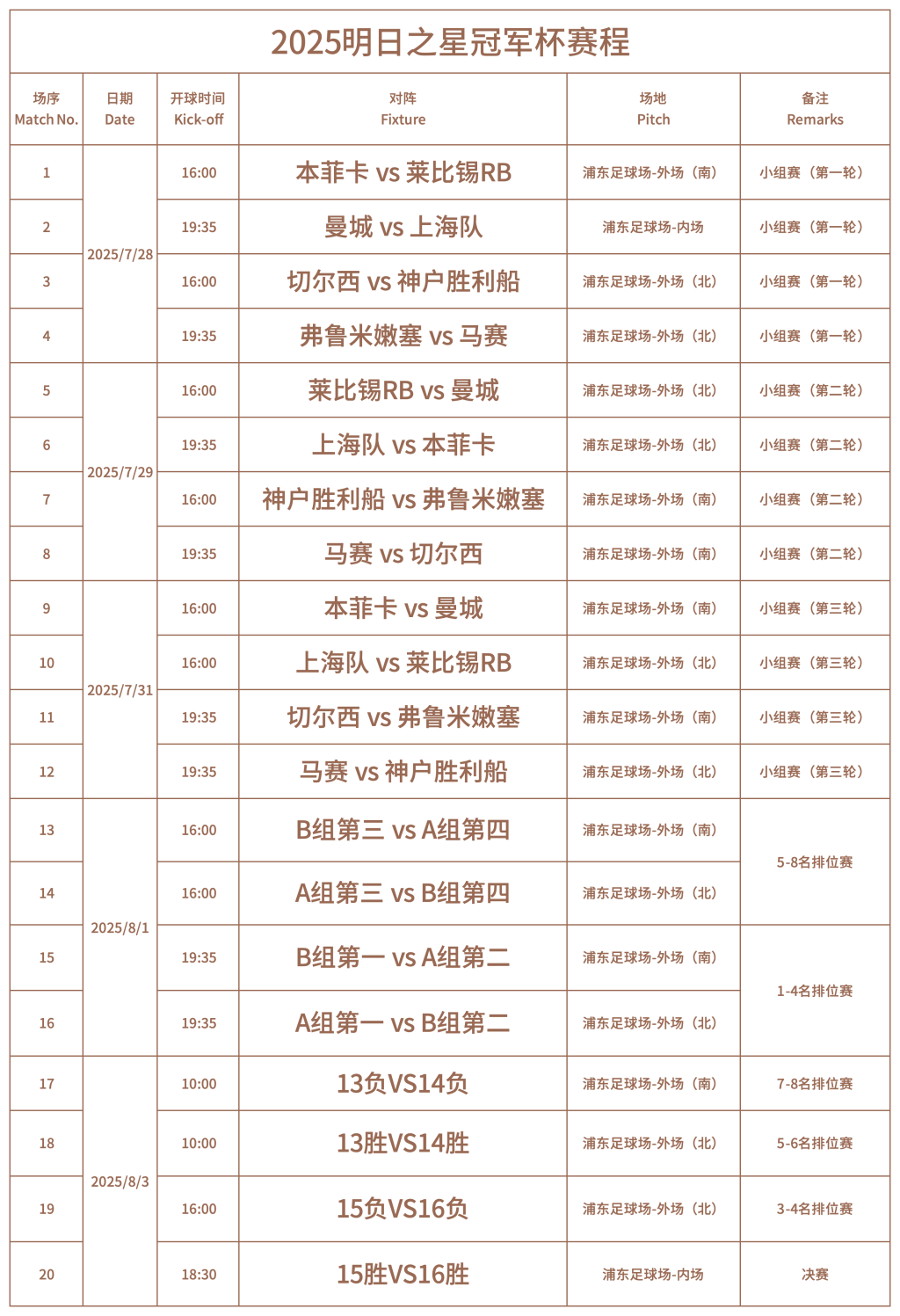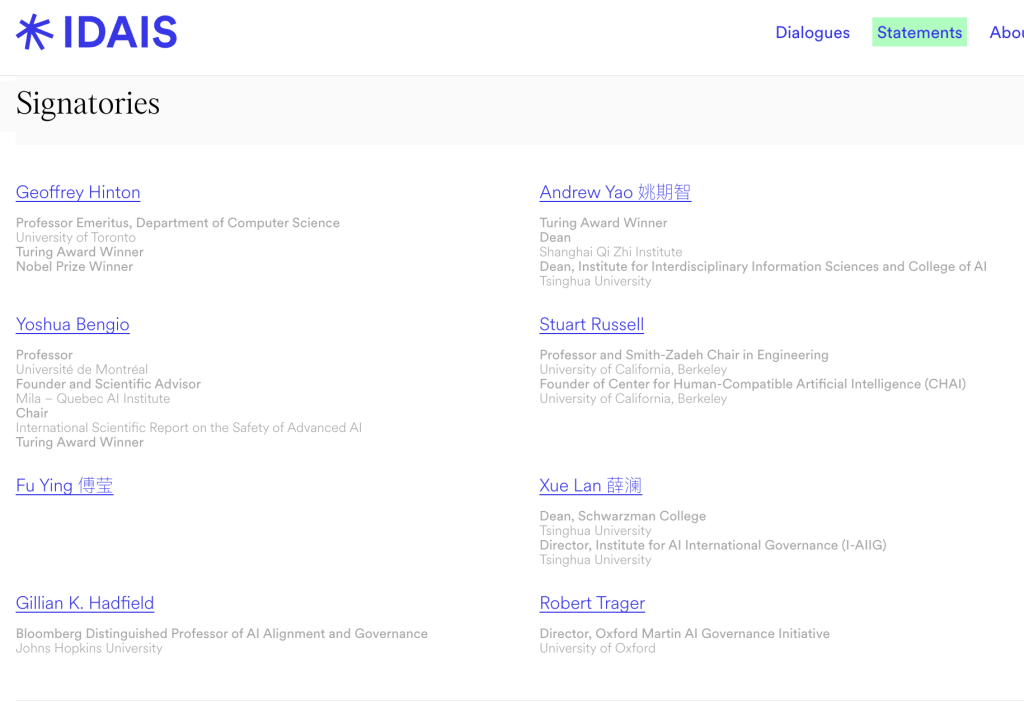天津地方志的修纂史上,高凌雯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民国《天津县新志》的总纂,其所著《志余随笔》实乃修志的经验之谈。高凌雯,天津人,字彤皆,清末生民国卒,清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志余随笔》为学者所重,来新夏先生点校该书,并为之作《前言》,称赞该书“资料搜集之广,尤可为修志者法”,其中引用谱牒资料颇多,于此可见族谱有资于修志。反之,从地方志也可了解其所利用的族谱情况,并从所记内容进入地方历史,特别是居民的历史。因此,笔者意在通过分析《志余随笔》所引谱牒资料,探讨天津人族姓的由来、族谱状况以及谱志的关系。
《志余随笔》所引谱牒史源及其考证人物价值
高凌雯说编纂天津方志时,“各家谱牒寓目者凡三十二姓,皆于选举荐绅人物,有资考证”。可见他利用谱牒修志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谱牒有助于选举、职官、人物的编撰与了解。他所寓目的谱牒应是当时天津存世的主要族谱,有32姓之多。直接引用的谱牒姓氏,有靳氏、李氏、梅氏、陈氏、黄氏、殷氏、费氏、倪氏、赵氏、武氏、华氏、邵氏、金氏、徐氏、刘氏共计15姓,占到所寓目者的一半。
高凌雯修志,很注意用谱牒资料作为证据。如志稿中有李瑞璋,即“据李氏家乘为之”。无谱牒资料为据,修志或有缺憾。如张霪的父亲闻予,有弟名念兹,惜“张氏宗谱已佚,若闻予、若念兹,皆不能举”。谱牒保存资料的功用明显,高凌雯便说:“明人文字,传于今犹可得见者……《津门诗钞》存刘公诗三首,云得自刘氏家谱。”
高凌雯看重谱牒的重要原因是谱牒人物资料往往根据碑刻,比较可信。如他说:“靳氏家谱谓其先人仕卫职有功者,事迹载城楼碑。”靳氏从城楼碑考证先人仕卫职有功,高凌雯在方志中采用靳氏家谱。再如,“北仓赵氏,原籍江南。永乐二年有名赵全者,以指挥使自会州卫迁武清,此赵谱所载,而《天津卫志·官籍》载有赵金、赵德全,俱江南人。则金或全之误……则赵全或即赵德全亦未可知”。这是依据谱牒推测卫志记载错误的事例。
但是,谱牒记载并不一定严谨,甚至前后矛盾,需要辨正。如“县志《殷尚质传》亦录卫志,其死绥一节,则采《明史稿》。公亦有墓碑,且近在城西,人亦未之知也。最奇者殷氏族谱开首即录碑文,大书‘予谥忠勇’,而县志沿《明史稿》之讹,作‘忠愍’,殷氏子孙又沿县志之讹亦改称‘忠愍’”。殷尚质事迹见于《明史稿》,记载尚质死后谥为“忠愍”,但是城西尚质墓碑记载其谥为“忠勇”,当以墓碑记载为是。县志采《明史稿》误,殷氏族谱录碑文又据县志改订,反误。又如,“黄东为钊长孙,明明载诸墓志,卫志谓东袭指挥佥事,升都指挥佥事。黄氏族谱,既载墓志而世系竟无东名,亦可异矣。且以承袭年祚远近计之,必东以下再有一世,方能衔接,是谱中断二世”。这些谱牒编纂者虽然搜集了比较原始的资料,但是疏于考证,行文中常出错误。
谱牒也记载有根本就不准确的,需要谨慎辨别,不能拿来就用。如“李经世附传,采自李氏家谱,其事其文,居然小说也。余为别缀以词,庶可避俗就雅,若直录之,则真豆棚瓜架之谈矣”。在高凌雯看来,李氏家谱中李经世的记载类似传闻,如果直接采用将成为民间笑谈,所以他特加说明,以免误导。
有的家谱甚至攀附名人,不足采信。高凌雯举例:“有人持家谱请著录,乃前明开国勋臣,累世禁卫大臣,鼎革且有死节者,此胜朝望族也。然卫志修于康熙初,距明不及三十年,阀阅之盛,并无一言及之,是为可疑。”c这种谨慎求真的态度,保证了高凌雯修志既利用谱牒又不轻信谱牒的恰当做法。
由于高凌雯看到谱牒当中的碑刻墓志传记资料,有助于修志存史,他在《天津县新志》卷二四单列“碑刻”一类,其中就有采自于《徐氏家谱》的《徐城墓志铭》《徐嘉贤墓志铭》。
《志余随笔》所见高凌雯对于谱牒学的见解
高凌雯通过阅读天津的谱牒文献,特别是修志中的考辨,对于谱牒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他认为,谱牒世系的长短、本旁支的详略,关键在于家族是否有老谱,世系不可靠的主要原因在于修谱者对祖先的记载出于追溯,他说:
明卫官家有谱者梅氏,世系太长(开国永乐已传三世)。陈氏世系太促(永乐初至明末仅历四世)。黄氏世系中断,殷氏、靳氏、费氏,大率仅载世系本支而旁宗不及,盖皆前无谱由后追溯,故叙述不详。惟倪氏具稿稍先,在明末已有底本,分支别派,尚觉清晰。余阅诸家谱牒,往往有创无因,尝有浅论以为修谱有法固善,否则宁详毋略,纵不合法,亦胜于无,所要者订年续修,莫令失坠耳。
有创无因造成世系记载不准,因此修谱要宁详毋略,订年续修,保留历史记忆。
谱牒记载如出于追溯,更加之文学形式,会影响史料价值,修谱应当避免。高凌雯讲道:“靳氏自永乐北迁,累袭卫职。至乾隆初,始立谱,子孙追述祖德,不以记传而以七言歌行出之,故事迹隐而不著。”
也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高凌雯认为民间修谱与“官谱”应有所区别,在于知祖先、明亲疏、详记载,而非明嫡庶、名位贵贱。高凌雯比较欧阳修所修族谱与清代族谱说:
欧阳文忠公辑族谱,但书名缀世系而已,盖犹官谱旧式也。今谱必书字及妻室、生卒年月日时、葬地方向,或病其繁赜,谓为不古,非也。盖古者世官之制,谱掌于官,仅以记宗支,明嫡庶,使无淆乱。今谱藏与家,欲使子孙详知其祖先,油然动追远之思,故不嫌繁琐,此时势之异也。惟谱以明亲疏,不在名位贵贱,今有详叙官阶使后人生轩轾之心,已失谱意。又有于名下论赞数语,类于注考,更失谱法矣。
古今异势,应理解今人,不必一定以古绳今。
因谱牒资料有助于修志辨别人物,族谱最好将传记资料别为一编。高凌雯指出:“科名、仕宦、封赠,皆最荣幸难得之事,凡祖先既有者亦不可湮没,修谱者应与传志、行状,别为一编,附谱而行,以存一家掌故。”
高凌雯认为,谱牒记载人物要详略得当,官绅尤为重要。他说:“明以卫官治卫人,官即绅也。上下相习,疾痛相关,勤于职者,必不乏人。卫志简略,遗迹多湮,其见于诸家谱牒者若殷氏、靳氏、梅氏、黄氏,则又详者不要,要者不详。”即要者应详,不要者或可不详。
天津人的由来:入籍与定居
天津地区的居民历史虽早,但是设立官府则较晚。金朝有直沽寨,元置海津镇,明改天津卫,清割静海、沧州、武清为天津县。自明永乐年间得名“天津”,随后明设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天津卫,英宗时建城,始见城市雏形。
天津城市史应当是从明朝正式开始。高凌雯对此有深切的感受,他说:“天津户籍最早者,大率由永乐迁来。”指的就是卫籍军户是天津人重要来源。《志余随笔》列举了不少事例说明天津族姓来源于明永乐时期迁来的卫所军人。如黄氏:“黄胜以燕山卫所总旗,从靖难军立功,累升指挥佥事。永乐二年,调天津左卫,管卫事。”再如梅氏:“梅氏为明驸马都尉梅殷后,及读其族谱,世系极详。梅殷生景福、景福生敬,敬生满儿,为天津卫指挥使。满儿为太祖命名,其调卫当在永乐二年……梅谱原起于满儿,其于殷则追书之,殷次子景福见《明史》,景福子敬未知所据,然梅氏必不伪造,或者满儿于殷为曾孙行,系出别支,年远遂有传闻之误耳。”又如陈氏:“陈氏族谱载,始祖一青,二世进,三世以智,四世应夏。应夏县志列入国朝人物。案:一青自永乐二年以千户调天津,证诸官籍,确载其名,而传之国初,其间只历二世,恐有阙失。”此外,本节第一部分提到的北仓赵氏,永乐二年赵全以指挥使自会州卫迁武清。
永乐之后来津的军人也陆续入籍。如武氏:“武嵩龄,大同人,明季官指挥佥书,管城守营事,擢辽阳都司。鼎革后,以天津为其旧治,移家居焉。有子七人,孙二十人。其谱牒自嵩龄以下甫三世而已断,今天津武氏多其后裔而莫能上溯矣。”再如倪氏,“卫制先入学而后袭官者有之,如尚殷质是也。倪氏家谱载倪思立万历二年武进士,袭职与发科不应相距三十年之久,二者必有一误。且已袭官,能否许应乡会试,其制已无考”。显然倪氏可袭官,原本属于军籍。
明代因经商等原因来津定居者也有。如“华氏有由嘉靖间迁来者,曰北华,其发科自华典始;一支由康熙初迁来,曰南华,其发科自华兰始,两系同宗,原籍无锡,惟西南华家庄,别为一族,与城华不相涉”。
清朝废除明朝的卫所,在天津设立行政机构县州府,天津的城市性质更加突出。各地来津的族姓增多,如“邵氏本姓刘,新莽时改姓周,后又冒姓邵。其族谱云,顺治初充务关掾,康熙元年务关移天津,与之偕来,遂入籍。以此可证务关南移之日”。明朝运河有七大钞关,武清县河西务是其中之一,清康熙初钞关从河西务移驻天津,划归天津道兼理。邵氏原在河西务税关任职,亦随务关迁移而入籍天津。又如金氏:“金公平,谱名安平,康熙间自会稽来天津……若金镕、若金溎荥、若金铭,虽同姓而各为一族矣。金溎荥之后今在太原,金镕即金刚愍公父,其族繁衍,自山阴迁天津,其谱牒上起于元,绳绳继继,派别厘然。”金公平是清康熙间自浙江会稽迁来天津的。
外地来津定居者不少是冒籍者。冒籍主要因科举考试为盐商、灶户设籍而产生。高凌雯说:“商、灶两籍,肇自明代。商籍为盐商子弟侨居而设,日久遂开冒籍之门。凡客游兹地者,因其亲族,缘引入场甚或异姓投考,至中式后有改归原籍之例,因以复姓,后以冒滥裁革,而灶籍如故。灶籍为沿海州县灶户而设,弊在一人而备二名,于此试之,未售者再于彼试之,谓之跨考。”冒籍的具体事例,如“徐金楷初名金楷,俞金鳌初名金鳌。旧志选举班可考。当是金氏入籍早,其后浙人来此冒籍者,因以冒其姓也”。
总而言之,高凌雯对于谱牒资料与修地方志的关系有清醒认识,他尽可能利用天津的谱牒,作为《天津县新志》重要的史源,同时对于谱牒记载多方比证,谨慎采纳,保证了《天津县新志》的质量。高凌雯修志过程中得出对于谱牒以及与地方志关系的看法,也是关于谱牒学、方志学的珍贵经验之谈。《志余随笔》颇多记载高凌雯寓目的谱牒资料,为我们了解天津的谱牒留下了珍贵的记载。根据高凌雯《志余随笔》所记谱牒资料,我们也了解到天津的族姓由来与城市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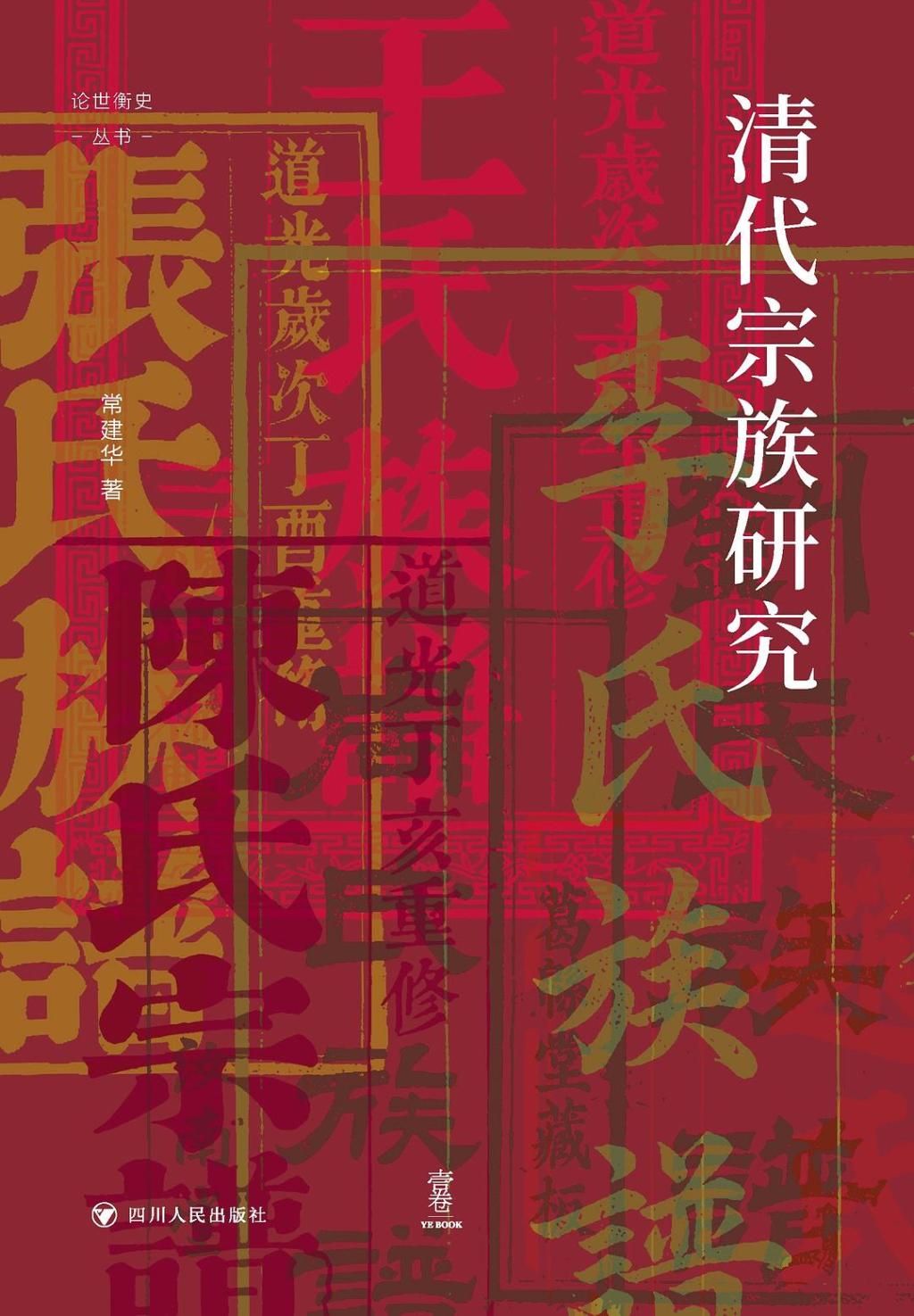
(本文摘自常建华著《清代宗族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