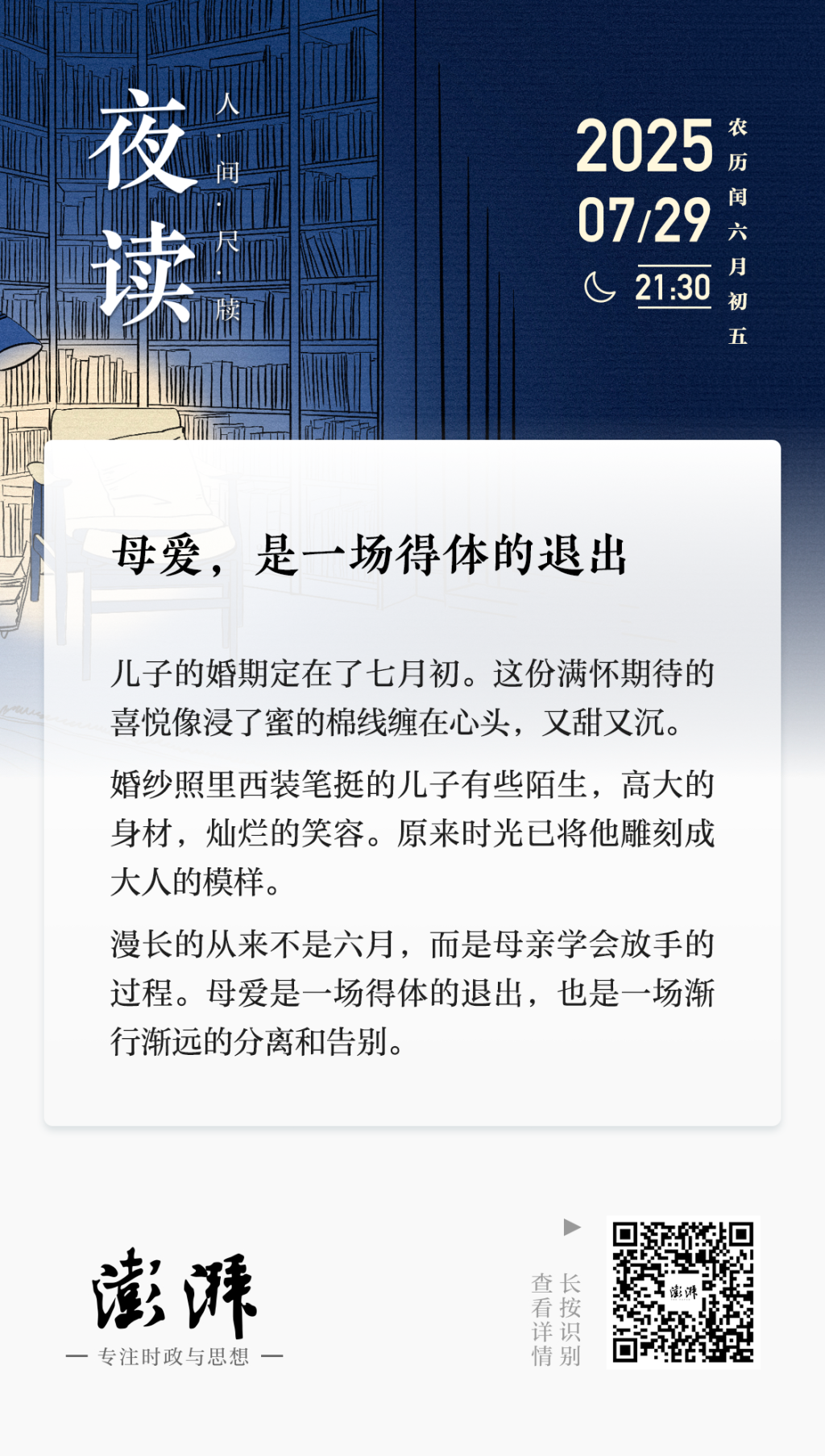今年有两个农历六月,这是我早在去年就知道的。但今年的六月,过得格外漫长,让人始料未及。
儿子的婚期定在了七月初。这些日子,我常在晨光熹微时醒来,望着窗外渐亮的天色发呆。这份满怀期待的喜悦像浸了蜜的棉线,缠绕在心头,又甜又沉。
我是个急性子的人。年轻时做记者,采访以快闻名,写稿也总是第一个完成。后来嫁了人,生养孩子,也是风风火火。儿子小时候常说我走路像踩了风火轮,说话像放鞭炮。可这个六月,把我的急性子磨得服服帖帖。
为了挑一床称心的大红四件套,我耐心地跑遍了大半个城,细致得像在挑选自己的嫁妆。手指在无数的棉绸上流连。红的太红,像未出阁姑娘的嫁衣,太过鲜艳;暗的又太暗,失了新婚的喜气。最后在老字号相中一床,那红恰到好处——既不过分招摇,又不失端庄大气,像极了我们这样人家该有的体面。
金线在红绸上流转,龙凤在风中起舞,我仿佛能看见往后的日子:晨光里,儿子和媳妇在这片喜红中醒来;暮色中,这抹红色会温柔地包裹着他们的梦。我轻轻抚平被角,突然发现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原来,这大红四件套里,藏着一个母亲半生的念想和期许。
六月的雨说下就下,近期的雨更是缠缠绵绵。想起儿子小时候,也是在这样的雨天,写完作业,非要出去踩水坑。我怕他着凉,硬是拦着不让。他便坐在地上蹬腿大哭,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如今想来,那哭声竟比这雨声还要真切些。
厨房墙上的身高线还在。最底下那道歪歪扭扭的铅笔印,是他五岁时我划的。那时他总踮着脚问:“妈,我长高没?”后来划痕越来越高,直到十八岁那年,我要踩着凳子才能够到他的头顶。
两年前的春节,儿子把他的心上人领回了家。我们做了一大桌子菜招待。那姑娘漂亮又懂事,声音甜美,看儿子的眼神像含着蜜。我们自然是满心欢喜。
儿子给她夹菜,那动作熟稔得让我陌生。我这才惊觉,他早已不是那个吃饭时会把米粒沾到脸上的小男孩了。他的手掌宽大了,肩膀厚实了,连笑声都变得低沉。而我记忆里的他,仿佛还是个小男孩,还停留在需要我的年纪。
六月的夜晚,月色正好,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忽然想起儿子出生那晚也是这样的月色。那晚我疼得死去活来,却在看见他的第一眼时就笑了。软软糯糯的他,像甜甜的棉花糖,瞬间融化了我的心 。如今他就要成为别人的丈夫,将来还会是别人的父亲。而我,将不再是他的全世界了。
再有几天便是儿子的婚礼,婚纱照里西装笔挺的他忽然有些陌生,高大的身材,灿烂的笑容。原来在我不经意的岁月里,时光已将他雕刻成大人的模样。
风吹纸动,六月的日历挂在墙上,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婚礼的筹备事项。我轻轻地撕下它,露出崭新的七月。
这一刻忽然明白:漫长的从来不是六月,而是一个母亲学会放手的过程。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也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分离和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