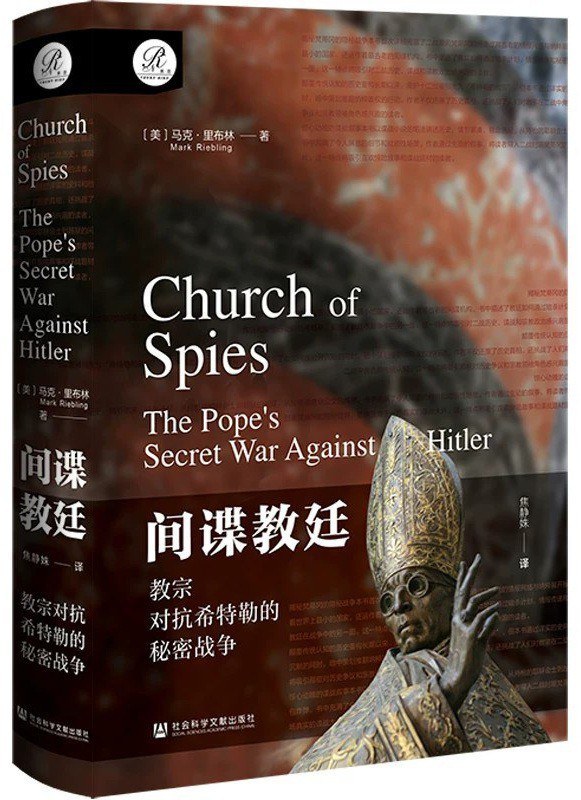
《间谍教廷:教宗对抗希特勒的秘密战争》,马克·里布林著,焦静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409页,89.00元
1940年3月11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在梵蒂冈迎来了一位不得不见的“不速之客”——时任纳粹德国外交部长的里宾特洛甫,此时,他正处于权力巅峰。不久前,他刚因为成功促成《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而深受希特勒器重。自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欧陆的西线战场一直处于诡异的对峙局面中,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此时也尚未对英法宣战。里宾特洛甫此行的最大任务自然是劝说墨索里尼尽早正式对英法宣战,而仅次于此的任务便是与教宗庇护十二世(尤金尼奥·帕切利)会面。
1938年5月,希特勒访问罗马时,教宗庇护十一世选择离开梵蒂冈和罗马,去了东南面的甘多尔福堡,借此回避与希特勒会面的可能性。用庇护十一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不愿意留在一座会悬挂“敌视基督的异教十字旗”(即纳粹万字旗)的城市。相较于自己的前任,庇护十二世对与纳粹最高层会面持开放态度,这或许与他曾长期担任梵蒂冈驻外使节、国务卿,负责外交事务的经历有关。早在1933年时,他就曾推动梵蒂冈与德国就天主教地位和教会权力问题签署过一份所谓“政教协约”,但之后的纳粹政府却并未遵守这份文件。在庇护十二世当选为教宗后,欧战随即爆发,当时的他至少在表面上决定效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本笃十五世的做法——即维持中立。

庇护十二世
长久以来,梵蒂冈及教宗本人如何看待法西斯运动以及纳粹德国都是一个引人关注且敏感的话题。早在战争结束前,就有不少人将庇护十二世没有公开明确批判纳粹暴行视为一种纵容乃至包庇,也认为天主教会是为了自保选择向“暴君”低头妥协;至于庇护十二世,则可能有“同情”纳粹及反犹倾向。这类观点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一度成为主流,如犹太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änder)的《庇护十二世与第三帝国》(Pius XII and the Third Reich)便是其中代表。在这本出版于1966年的专著中,弗里德兰德为读者们绘声绘色地描绘了里宾特洛甫与庇护十二世会面的场面:纳粹德国政府向梵蒂冈提出了与西方盟国和谈的所谓条件,而梵蒂冈则在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与柏林达成了共识。希特勒还希望在西线发动大规模攻势前,将庇护十二世拖入这场分赃游戏。弗里德兰德认为,这可以解释日后庇护十二世为何在战争中选择无视犹太人大屠杀等纳粹暴行,并在公开场合保持所谓“沉默”。1999年英国记者约翰·康维尔(John Cornwell)在专著《希特勒的教皇》(Hitler's Pope)中再度重复和强化了这个观点。
不过,无论是梵蒂冈方面的档案,还是德国或意大利方面的档案,都并未找到能够坐实弗里德兰德书中描述的相关记录。实际上,站在纳粹德国的角度来看,1940年3月的这场会谈并不是一场“成功”的外交会谈。对当时的纳粹德国来说,里宾特洛甫的造访更多是出于外交宣传的考虑,此外则是为了安抚、拉拢德国、意大利境内的天主教徒。会谈中,里宾特洛甫向庇护十二世转达了希特勒的话:“国家社会主义与天主教会之间达成基本和解是完全可能的。”庇护十二世对此的回应则是一份记载德国天主教会如何遭受迫害的备忘录,并直白地指出:“事实表明,德国正在发动一场针对教会的战争。”在其他问题上,里宾特洛甫同样未能说服庇护十二世相信德国的全面胜利即将到来,后者再三表达了对波兰的同情。当里宾特洛甫指责“波兰的神职人员只顾着参与政治,反对德国人”时,庇护十二世则表示:“可以要求波兰神父保持沉默,只专注于他们的牧职,不给占领当局制造麻烦,但不能指望他们放弃对祖国的热爱。”
不难想象,这场会谈最终近乎不欢而散。
事后,纳粹德国外交部没有发布任何关于这场会谈的公报和新闻稿,以至于当时的国际社会围绕会谈内容产生了大量猜测。有人认为这是“纳粹的胜利”,也有人认为这是“卡萨诺之行”的翻版,还有人认为这是柏林方面最后的警告,等等。至于梵蒂冈方面,虽然也没有发布关于这场会谈的官方公报,却以另一种形式婉转地表达了态度。在会谈后的12、13日,庇护十二世连续两天在公开讲话中强调正义与和平的重要性,不点名地要求德国纠正不正义的行为,如此方能实现和平。这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远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教宗在与里宾特洛甫的会谈中代表德国和波兰受迫害者发声”的报道。3月17日,庇护十二世在给德国枢机主教们的信中写道:“从人类的角度而言,目前我们看不到任何有利于和平和德国教会处境的迹象……”单从1940年3月的这次会谈,就不难看出庇护十二世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不与纳粹德国公开对抗,但以一种隐蔽和间接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事实上,庇护十二世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努力可能还远不于此,他甚至曾以更秘密的方式直接参与了反对希特勒的战争。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关于如何认识庇护十二世以及梵蒂冈在二战期间所扮演的角色,逐渐有了更多元的观点和解读。如情报研究专家、历史作家马克·里布林(Mark Riebling)的《间谍教廷:教宗对抗希特勒的秘密战争》便希望通过对最近三四十年来陆续解密的档案的系统梳理,来挑战乃至推翻有关庇护十二世与纳粹同流合污的指责——他在书中所呈现的内容恰恰与之相反:庇护十二世是一位暗地里运营着反纳粹情报网的“间谍大师”。
在里布林所搜集的资料中,有两部分特别引人注目。
其一,是梵蒂冈方面尤其是庇护十二世的监听录音。在被选为教宗后,庇护十二世便决定在自己的书房安装监听设备,以便录下他与访客的对话。当然,监听工作也并不局限于教宗书房,而是可能在梵蒂冈的任何一个地方,例如西斯廷教堂的某个阴暗角落。里布林将这些录音称为“梵蒂冈保守最严的秘密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才逐步为人所了解。其二,则是原美国中情局反间谍主管詹姆斯·安格尔顿(James Angleton)所搜集的情报文件。二战前后,安格尔顿曾是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罗马站的负责人,曾通过各种方式搜集了大量涉及庇护十二世及其亲近人士的资料。顺便一提,这位安格尔顿先生当时也是英国军情六处高级官员、日后被证明是苏联间谍的金·菲尔比的亲密好友。从安格尔顿搜集的这些资料中,可以窥见庇护十二世在战争期间是如何运作梵蒂冈情报网的。
首先,这个情报网之所以能成立,有赖于德国国内的反纳粹势力。早在1939年秋天,德国国防军内部反希特勒的军官们就开始尝试与庇护十二世建立秘密联系。一方面,这是因为这群军官中很多人都有天主教的信仰背景。例如1944年7月差点成功刺杀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便是天主教徒。在与这群反希特勒的军官取得联系后,庇护十二世甚至还在宗教上给刺杀行动开了“绿灯”。这位教宗曾告诫这些军官:根据天主教教义,公民可以刺杀“不公正地使用权力”的暴君,而希特勒正属此列。他们可以在希特勒的飞机上安装炸弹,这是为了与邪恶斗争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德国国内的反纳粹者们还相信梵蒂冈可以通过遍及全世界的网络向同盟国方面传递信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或许是德国国防军情报局(阿勃维尔)的首脑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海军上将。在波兰前线目睹党卫军的种种暴行后,卡纳里斯便决心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职位,致力于推翻希特勒和纳粹的统治。而与梵蒂冈和庇护十二世建立直接的秘密通信渠道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事实上,卡纳里斯与庇护十二世是老相识。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就认识了当时是宗座驻德国大使的庇护十二世。卡纳里斯非常欣赏庇护十二世的谨慎、现实主义以及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反感。于是,在1939年底,一位来自巴伐利亚的律师、一战老兵以及虔诚的天主教徒约瑟夫·穆勒(Josef Müller)就成了卡纳里斯与庇护十二世之间的秘密信使。这位艺高人胆大的巴伐利亚壮汉冒着天大的风险多次穿梭于德国与梵蒂冈之间,甚至会亲自开着小型飞机来运送秘密文件。为了掩护与梵蒂冈的联络行动,卡纳里斯将其伪装成了国防军情报局的另一项秘密工作:监视意大利境内的“反德人士”与“和平主义者”,而穆勒则是被招募来执行这项工作的外围特工。实际负责与穆勒接头的则是庇护十二世的私人助手德国籍主教罗伯特·莱伯(Robert Leiber)

威廉·卡纳里斯

约瑟夫·穆勒
正是通过卡纳里斯-穆勒这一渠道,庇护十二世得知德国内部有一股反纳粹势力试图刺杀希特勒本人。他在1940年初,就秘密向英国政府告知了这一情况,并表示愿意充当德国反纳粹势力与同盟国之间的中间人。此外,庇护十二世也通过美籍的耶稣会传教士与战略情报局向美国传递了相同的情报。
1940年5月6日,纳粹德国在西线发动全面攻势的前夕,威廉·卡纳里斯和约瑟夫·穆勒想方设法向梵蒂冈秘密传递了这则军事情报,内容非常详细,包括进攻时间、部队部署等。7日,庇护十二世则派自己的助手将此情报告知法国的外交官:未来三四天内,德国将大举入侵低地国家,还提供了“预期作战方式的战术情报,包括伞兵和破坏行动的部署情况”。同时,庇护十二世也通过其他渠道直接向比利时政府发出了预警,并亲自向比利时公主玛丽·何塞转达这则情报。不过,显而易见,无论是法国还是比利时都未能重视梵蒂冈方面传来的情报或者根本来不及做好准备。
除了组织军事和政治情报网络外,庇护十二世还从穆勒传递的报告、照片乃至电影胶片中得知了纳粹在东欧各地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庇护十二世曾称希特勒“不仅是一个不可信赖的恶棍,而且还是一个从骨子里就邪恶的人物”。当他获悉纳粹执行了大规模、有系统的屠杀时,甚至曾像孩子那样流泪痛哭。然而,当西线战役正式打响,尤其是意大利正式参战后,梵蒂冈便如一叶海上孤舟,深陷轴心国的包围之中。这或许正是庇护十二世在公开场合对纳粹暴行保持沉默的根本原因。
里布林认为所谓“教宗的沉默”其实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战略选择,而且当时德国国内反希特勒的势力也希望庇护十二世能保持沉默,以避免德国国内的天主教徒沦为报复的牺牲品。与之相对,一向厌恶天主教会的希特勒甚至可能希望梵蒂冈公开发表谴责纳粹的言论,如此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像“碾碎蟾蜍一样碾碎教会”。长期从事外交事务的经验无疑形塑了庇护十二世现实主义的处事策略,这与身为宗教组织领导人的道德责任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张力。虽然在表面上保持着沉默,但庇护十二世不仅维系着一张跨国的反纳粹情报网,也曾多次在外交上忤逆希特勒的要求,正如他与里宾特洛甫会面时所做的那样。例如,他曾拒绝接受纳粹德国派驻梵蒂冈的大使——纳粹党的老牌政治盟友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里布林在《间谍教廷》中以大量资料为基础、用引人入胜的生动笔调为我们讲述了这场庇护十二世所参与的“暗战”,但并不意味着庇护十二世本人以及梵蒂冈在二战期间的所有政策和行为均无可指摘之处——实际上,无论是“公开的沉默”,还是拯救犹太人的努力程度以及二战后对旧纳粹分子的态度,仍有不少值得商榷、讨论乃至批评的地方。庇护十二世如何通过各种秘密手段重新加强教宗权威,也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主题。
另外,如果对梵蒂冈的情报史感兴趣,还可以参考另两位学者的研究,分别是大卫·阿尔瓦雷斯(David Alvarez)的著作《梵蒂冈的间谍:从拿破仑到大屠杀的间谍活动与阴谋》(Spies in the Vatican: Espionage and Intrigue from Napoleon to the Holocaust)、伊沃纳尼克·德诺埃尔(Yvonnick Denoël)的《梵蒂冈间谍:从二战到教皇方济各》(Vatican Spies: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Pope Francis)。这两部著作都从更宏观的角度和长时段的维度描述了梵蒂冈如何通过隐秘手段悄然影响着国际局势的走向,可以弥补更多《间谍教廷》中未涉及的主题,其中不乏“惊人的阴谋”与“肮脏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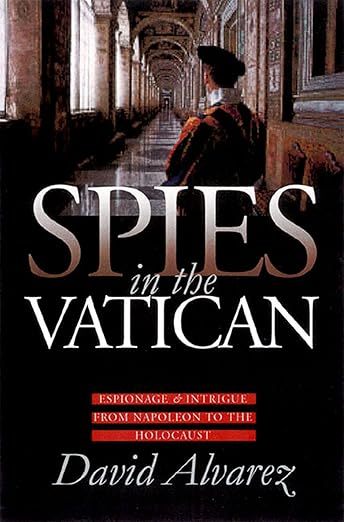
《梵蒂冈的间谍:从拿破仑到大屠杀的间谍活动与阴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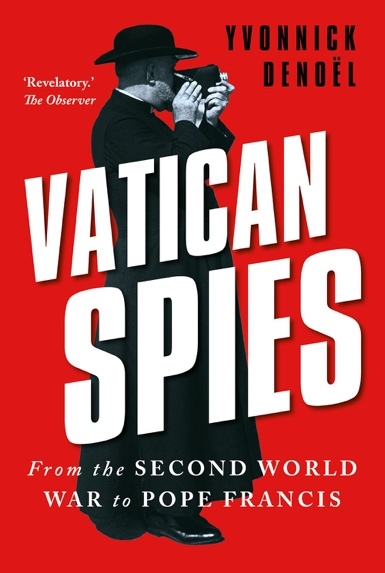
《梵蒂冈间谍:从二战到教皇方济各》
至于究竟如何看待庇护十二世本人在二战期间的行为,或许可以用他本人的话来总结。
1939年3月6日,刚当选不久的庇护十二世在自己书房接见了惴惴不安的德奥主教们。监听设备录下了这场会面的对话。在会面结束时,庇护十二世告诉主角们:
我们不能放弃原则……如果他们想战斗,我们也不要害怕。但我们还是要看看是否有和平解决的方法……如果我们试过所有方法,他们坚决要战斗,我们也一定会反击。如果他们拒绝,我们必须要战斗。
《间谍教廷》正是通过精彩的文本和缜密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庇护十二世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并投入这场秘密战争之中。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