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经济学者徐瑾的最新力作《软阶层》今年6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正式出版,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理解和应对时代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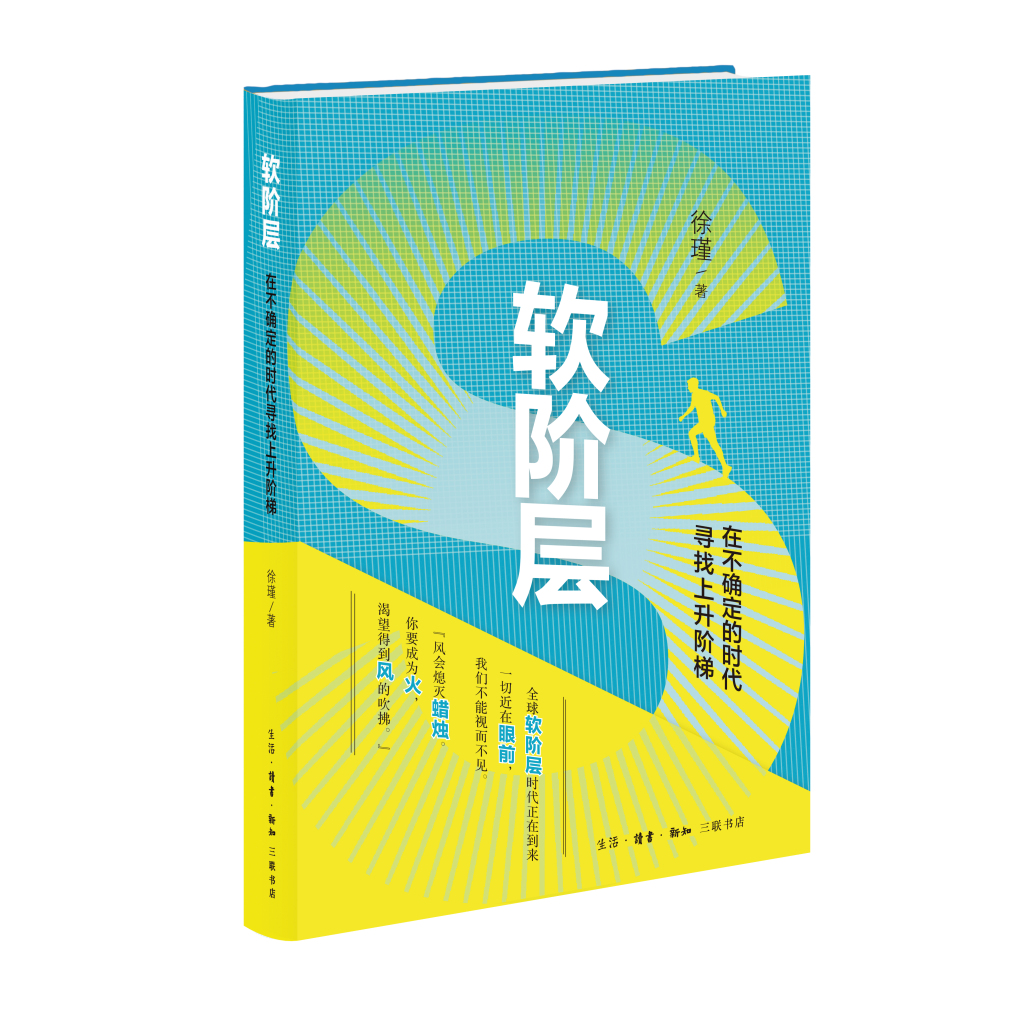
《软阶层》书封照
徐瑾曾出版多部畅销财经书籍,如《白银帝国》《印钞者》《凯恩斯的中国聚会》等。在书中,徐瑾独创性地提出了“软阶层”这一概念,用以定义那些在逆全球化时代根基不稳的城市中等收入群体。
书中详细分析了软阶层面临的四大核心困境:房产、职场、教育、性别。这些困境不仅是个体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缩影。面对软阶层的现实挑战,徐瑾认为,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个体需要重新定位自我,横向拓展兴趣与社交网络,以应对可能的风险和挑战。
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徐瑾表示,自己在专栏中首次推出“软阶层”概念是在2017年。“成稿至今也有七八年了,这本书可以说是随着‘软阶层’从预测变为现实才姗姗来迟。”
观察当下国内的经济学人,一面通过著书立说传播知识,一面又在个人供职的媒体平台和主理的自媒体平台、“读书会”社区同公众积极对话互动,徐瑾无疑显得很是出挑。而她本人的“斜杠人生”,也正是对如何破拆“软阶层”概念的最好诠释。
【对话】
“软者,柔也。”
澎湃新闻:如书名所示,你独创了“软阶层”的概念以定义“根基不稳的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为何选择“软”字概括其核心特征——我们知道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软”也常常体现为一种哲学思想和处世智慧。
徐瑾:在中国古文中,“软者,柔也。”软阶层之“软”意味着根基不稳。
不少人将软阶层社会理解为阶层固化社会,其实是一种误会——软阶层并不意味着可以坐稳中产的位置——它与传统的“阶层固化”概念不同,软阶层概念强调的是,没有阶层固化,更可能是阶层下滑。
我提出这个说法,不是在刻意扩散焦虑,只是一个观察和判断。
澎湃新闻:书中指出的房产、职场、教育、性别是软阶层的核心困境。若按破解紧迫性排序,在你看来哪一项是目前最难解决的?
徐瑾:每个人都是真实的个体,这意味着每个人的困境也都是独特的。这四种困境可能因人而异,也可能彼此叠加。我觉得从紧迫性而言,可能还是职场——对多数人而言,人有了工作,才有安身立命的底气。要解决“职场996”、“35岁危机”、情绪内耗等问题,问题恐怕在职场之外。
从这个意义而言,改善职场,其实应该从改善中小企业处境入手,它们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就业机会。综合自国家统计局、全国工商联、地方统计公报等权威来源,从“56789”这一数据框架来看,大概来说,一般认为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因此要改善职场困境,必须从支持民营企业入手。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那么多人都有机会进入大厂年薪百万或者进入体制,所以普通工作的改善更为关键。
澎湃新闻:软阶层是“全球现象”,相比欧美同样面临的“中产萎缩”,中国软阶层面临哪些独特的挑战?你又有哪些针对性的建议?
徐瑾:是的,中国软阶层其实有自身的特点。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成长太快了,几乎一两代人时间就走过西方数百年的道路。
对于中国软阶层而言,还是应该降低预期,降低杠杆。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丰富完善自己的社会网络,尽可能让自己的生活不要沦为原子化的境地。可以抱团竞争,无论是自己的家族,还是自己的社群,都可以成为自己又一个支撑。
澎湃新闻:技术革新是否正在加剧阶层“液态化”而非促进流动?
徐瑾:我们就以短视频平台为例,一方面,确实给予一些人出头的机会,这应该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如果抛开对其内容价值观等的审视,这对阶层流动是有帮助的。当然,这些人的成功有个人因素,有运气因素,也有平台因素。
另一方面,在任何社会的技术更新,至少在中早期,对于软阶层都存在弯道超车的机会。短视频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内容,而在于现在平台比较成熟,素人想出头比过去要难。
“迟做总比不做好,中年审视好过老年追悔”
澎湃新闻:作为财经观察者,你既剖析阶层焦虑又呼吁“清醒乐观”。结合你多年来媒体实操的经验,知识人应如何平衡情势示警与传递希望?
徐瑾:不少人喜欢以结果论成败,所以有句话是“悲观者常常正确,乐观者常常胜利。”其实所谓悲观者未必正确,而所谓失败的乐观者大家只是选择看不见而已。我觉得悲观和乐观都是基于事实而言,悲观基础之上的决策,可以报以乐观应对——所以我常常说,“悲观是一种判断,乐观是一种选择。”
同时拥有悲观和乐观,看起来矛盾,其实想想并不是。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充满灰色,一个人能够容纳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型,本身就是成熟的标志。我的背景是经济学,读经济思想史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这些大师到底是乐观还是悲观?凯恩斯这样的人自然是乐观的,哪怕是哈耶克、亚当·斯密这样看似悲观的大师,我觉得他们归根结底也是乐观的,因为如果他们是悲观主义者,也许什么都不会写,什么都不会做,他们恰恰对于人性有信念,才作出那么多伟大的作品。
澎湃新闻:书中提到“二手人生”作为软阶层的自救策略,强调横向拓展兴趣与社交网络。能否结合你近年来运营读书会、社群的经验,分享一个普通人成功开辟第二职业或建立风险对冲网络的具体案例?
徐瑾:“二手人生”意味着抛开原生家庭赋予的“一手人生”,重新定位自我。重新思考定位自己下半生。这对于很多东亚人尤其是一路升级打怪的做题家,也许更有必要。我们中不少人,总是忙于不断攀援的阶层游戏,却可能忘记自己为何出发,到底追求什么?如果我们在追求中再不尽如人意,可能就会感到加倍的失意,这往往是构成中年危机的起源。
当然,因为我们已经是成年人,所以不可能轻松上阵,说让当前的人生翻篇就翻篇,这个再定位的过程其实并不容易。我和社群里不少朋友都聊过这个话题,以前经历这个过程的人并不多,这些年大家也许没有了那么高的预期,也不那么急吼吼的,反而有了更多机会去审视自己的生活,更为切身地思考“二手人生”这个话题。
比如我有个朋友,在我写《软阶层》的时候,他公开的身份还是广告公司高管,私下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书评人。显然,他其实一直觉得自己的主业是前者,后者可能连副业都谈不上,毕竟收入连主业的零头都算不上,而且也不符合专业精英的人设。所以,在自己的工作场所,他对书评人这一身份避而不谈,甚至刻意回避自己喜欢读书的事。但这些年,他意外失业了,而且不止一次。他不得不拓展自媒体业务。这个过程中,意外的是,原来的专业身份没有起到关键作用,反而是书评人的身份给予他支撑,让他收获新的人生定位。根据我的观察,他现在活得也很自洽。
正因为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其中有觉醒,有痛苦,也有喜悦。“二手人生”意味着审视自我,抛弃更多虚假的人格面具,更为诚实地面对自己。这未必能够帮助你打赢阶层游戏,但是起码在你陷入软阶层困境的时候,可以更从容地应对和渡过。
作为普通人,“二手人生”可能意味着横向发展,也可能意味着重新培养一门兴趣,甚至是给自己一段空白的时间。我不认为每个人都要去做副业,更不是都要做自媒体,但审视自己内心,追问原来的道路是否真的自己需要的,这很重要。毕竟,迟做总比不做好,中年审视好过老年追悔。
澎湃新闻:书中强调“选择比努力重要”,这句话请你再展开讲讲。
徐瑾:面对时代变化,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理解是选择的前提。如何定义并且理解我们的时代,决定了我们社会的未来,也决定了我们个体的未来。
我觉得当下降低预期很重要,要走出别人框定的成功叙事。前些年经济狂飙,成就了不少上升梦,自媒体也对于各种财务自由故事推波助澜,这其实放大了大家焦虑。
现在宏观慢下来,各种叙事又换了一种,一会鼓吹离职“人生是旷野”之类,或者高喊进入体制就稳定云云。软阶层首先要改变的,恰恰是凡事都按照别人的剧本来走,要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否则会越来越焦虑,也越容易被收割。相较于环境的改变,改变自己则相对容易。我向来认为,一个人首先要明白自己为何而活——我们未必能因此而活得更好,但会活得更明白。
澎湃新闻:你常以经济史视角分析问题(如之前的著述《白银帝国》)。历史上的别国,比如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是否也有类似“软阶层”?其最终走向对今天有何启示?
徐瑾:我自己一直对日本感兴趣,最近十年都在整理日本经济史的内容,计划陆续出版“日本三部曲”。很多人都会问我类似的问题,就是日本对于中国的参考之类。我觉得对于东亚国家而言,日本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很多问题或者“坑”,日本其实都帮我们提前踩过一遍,比如房地产泡沫、过度投资、老龄化、女性贫困等等。
就软阶层问题而言,日本经验我觉得最大启发在于:一方面,日本是一个有阶层存在的社会,甚至社会上各个团体其实也都有自己的边界;另一方面,日本也相对平等,在法律、福利、看护等方面尽可能覆盖多数人。这些为社会兜底的举措,让日本经济哪怕陷入“失去二十年”,让软阶层哪怕在滑落之后,也能有所依靠,保留最后的体面。
当然,日本等国案例和中国也有蛮多不同。比如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人均收入就比中国高,也有一些积累,我们处理同样情况也许压力更大,显然早作打算肯定更有利。不过,问题还在于,有时候人类注定从历史中学不到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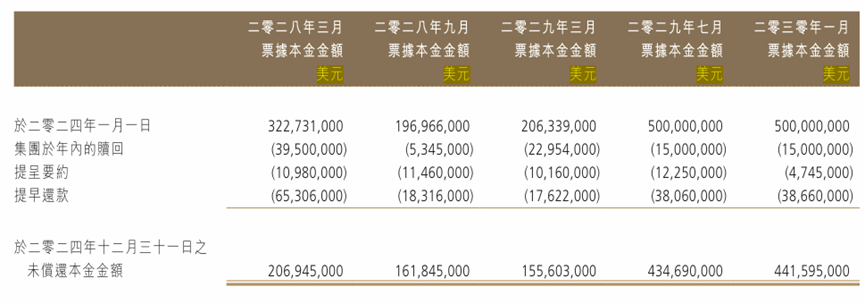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