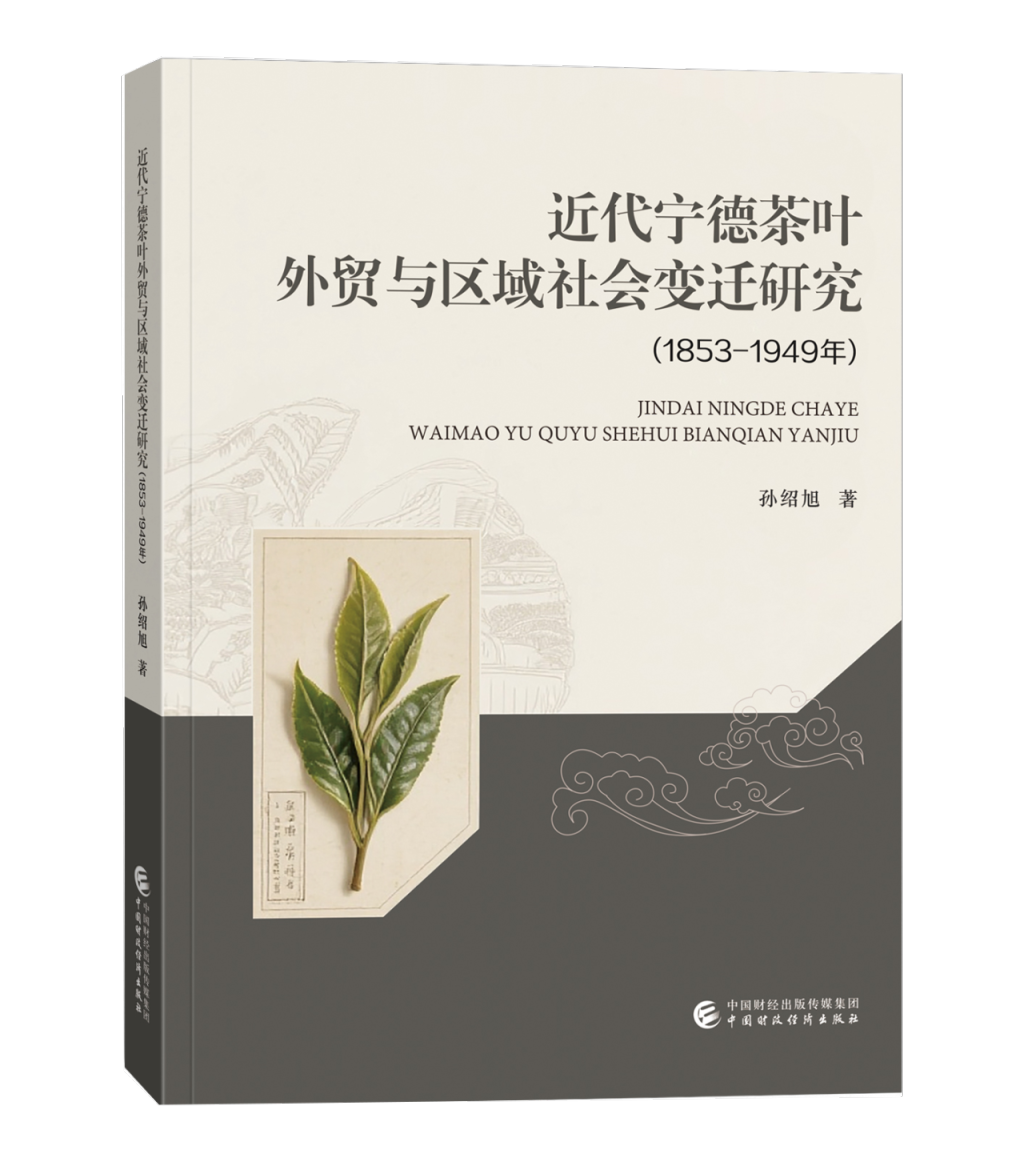
绍旭2016年考入华东师大历史学系,随我研习中国近现代史,2020年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这部著作即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我了解这本书从一篇学位论文到最后成书的全部过程,以及绍旭为这本书倾注的心血和感情,也了解这本书对他本人和闽东区域史研究的特殊意义。可能正因为如此,尽管我推辞再三,绍旭仍坚持要我在书前写几句话。
和许多博士生有所不同,绍旭读博之前就已是副教授,在闽东区域史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并矢志以此为志业,出版过《萌源古村》《白银古道》《周宁茶文化》等多部相关著作,论文更多,可谓成绩斐然,是闽东区域史研究领域有数的专家之一。多年前我曾为他的另一本著作作序,其中写道:
绍旭生在周宁,长在周宁,现在又供职于宁德,他对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满怀深情,对变迁中的家乡更负有一种深切的使命感。带着这种深情和使命感,十多年来,无论寒暑,无论雨晴,只要得空,便深入到实地进行调研。他常常行走在行人稀少、布满青苔的白银古道上,去亲近和发现一座座废弃的白银矿坑;他往来穿梭于大山深处的古村落世界,汲汲为破落且日渐稀少的古村落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存续之道;他当然更关注家乡在全球化时代的剧烈变迁,并把这种关注化作系统的论说,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模式。基于这些实地考察,再结合自己经年累月潜搜冥索所得的可观乡邦文献,互为参证,已陆续撰写并出版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实证分析——以周宁县百年劳务变迁为个案》《萌源古村》和《白银古道》等多部著作,在闽东这片几乎被学术界遗忘的土地上,逐步构建和拓展属于自己的学术版图,并为乡邦文化承传与发展倾注了自己的心力。据我所知,他今后仍将以闽东地区为中心,力求以更阔大的视野和更沉潜的学术定力,在已累积的基础上写出看得见的闽东和看不见的闽东,以展示这片土地的神奇和沧桑。
基于绍旭这样的研究基础和学术抱负,读博伊始,当他提出希望以闽东茶叶外贸与区域社会变迁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选题,我立马就同意了。当然,我之所以同意,还有另外一些更重要的考虑。具体而言,主要包括:
一、茶叶贸易本身的全球意义。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茶曾是早期全球化时代最受西方青睐且最具标识意义的中国商品,被誉为近代商业史中的“第一商品”“王牌商品”“全球性商品”,并长期占据中国出口商品的首位。一位19世纪上半叶在广州经营茶叶生意的美国商人说:“没有别的商品能像茶叶这样刺激国际贸易,也没有哪种饮品能带来和茶叶一样的利润,并让中国以外的文明国度都如此痴迷。”17世纪以后,西方“梯航万里”一路向东,最初主要就是为中国茶叶而来,可以说是茶叶把彼此悬隔的东西方两个世界连接在一起,也是茶叶把中国拖入欧洲主导的世界市场和全球化体系之中,就此而言,可以说中国茶“改变了世界历史”。正因为如此,有关茶叶贸易的研究向来备受关注,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史的兴起,茶叶贸易更成为海内外学界竞相研讨的全球性议题,英美尤为热衷,以茶叶贸易为主题的著作层出叠见,据陋见所及,单是已被译为中文的著作即有埃丽卡·拉帕波特的《茶叶与帝国:口味如何塑造现代世界》,艾伦·麦克法兰、艾丽斯·麦克法兰合著的《绿色黄金: 茶叶、帝国与工业化》,简·T.梅里特的《茶叶里的全球贸易史:十八世纪全球经济中的消费政治》、莫克塞姆的《茶:嗜好、开拓与帝国》,马克曼·埃利斯、理查德·库尔顿、马修·莫格合著的《茶叶帝国:征服世界的亚洲树叶》,马克曼·埃利斯、理查德·库尔顿合著的《十八世纪英国的茶与茶会》,萨拉·罗斯的《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艾梅霞的《茶叶之路》,刘仁威的《茶业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等。相比之下,理应在茶叶贸易史研究领域更具发言权的中国虽也推出一些出色的研究著作,如陈慈玉的《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与世界市场》《生津解渴:中国茶叶的全球化》,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周重林、太俊林合著的《茶叶战争:茶运与国运》,石涛等著的《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叶》等,但毋庸讳言,无论是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热度都存在显而易见的落差,与中国茶叶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尚不匹配。
二、茶史研究应更关注茶乡研究。如前所述,中国茶叶贸易史研究著作虽已有不少,但无论中外,均以宏观研究居多,对主要茶叶产区的微观细化研究明显不足,较具学术份量的著作仅见邹怡的《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和肖坤冰的《茶叶的流动:闽北山区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等,除武夷山、徽州外,其他茶叶主产区的研究至今几乎仍是一片空白,闽东就是一个显例。实际上,自1844年7月福州开埠以来,闽东因地近福州快速发展成为中国茶叶主产区和茶叶外贸区之一。研究显示,1860年代初,闽东茶叶输出量首超闽北地区,1890年代随着印度、锡兰(斯里兰卡)、日本等新兴产茶国的崛起,茶叶贸易的国际竞争加剧,中国茶叶外贸遭遇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这种大势下,闽东茶业亦不免受到严重的冲击,但随着1898年三都澳开埠,港口与腹地的联动更紧密,物流成本大幅降低,闽东茶叶外贸迅速止跌企稳,据1900至1948年间的福海关数据统计,闽东茶叶年均输出11万担以上,占全国输出总量的10.32%以上。受茶叶外贸的推动,闽东“各县除沿海一带,因海风剧烈,土壤多含盐质不宜种茶外,虽穷乡僻壤无不有茶树之种植”,茶区因此而大幅拓展,据1948年出版的《中华国货产销协会每周汇报》第5卷第46期刊出的《福建茶叶产销概况》所示,福建全省产茶地达33县,计1443茶区,闽东地区古田37茶区,福鼎80茶区,霞浦33茶区,寿宁140茶区,福安104茶区,宁德95茶区,周墩42茶区,柘洋28茶区,屏南90茶区,共计649茶区,占全省的45%。1934年福建全省茶叶产量9094300担,闽东5884810担,占64.7%;全省茶叶输出量201110担,闽东输出量142520担,占70.87%;1938年全省茶叶面积584365市亩,闽东茶叶面积244580市亩,占41.85%。这些数据表明,闽东在福建乃至全国茶叶生产和茶叶外贸整体格局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不但至今未变,而且仍在不断增强。闽东十大特产,茶占其三,分别是福鼎白茶、坦洋工夫、官司绿茶,其中福鼎白茶更居十大特产之首,并跻身中国十大名茶之列。闽东茶叶品种繁多,几乎每个县市都有自己的品牌,除福鼎白茶、福安坦洋工夫、官司绿茶三大特产外,寿宁乌茶、周宁高山云雾茶、霞浦元宵茶、柘荣长寿茶、古田红茶、屏南小种等,亦广受饮者青睐。闽东茶业规模长期位居全国茶叶主产区前列,近年来,闽东茶叶生产规模、茶园面积仍在不断扩大,茶叶产量、品牌茶叶价值不断增加。据统计,2020年,全区茶园面积95万亩,毛茶产量11.04万吨,毛茶产值41.95亿元。然而,已有的中国茶业史研究却很少涉及闽东,即使是有关福建茶业史的专门研究,对闽东茶业亦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近年来,这种状况虽已有所改观,闽东各县市陆续编辑、出版了一些茶叶志书和茶叶史料汇编,但总体而言与闽东作为中国著名茶乡的地位相比仍很不相称。
三、茶叶外贸与区域开发的关系研究值得重视。茶叶外贸不仅是闽东茶业发展的推手,也是闽东区域开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引擎。由于受地理条件的制约,闽东区域发展相对迟缓滞后,福州开埠,特别是三都澳开埠后,伴随着茶叶外贸和闽东茶业的发展,闽东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发展机遇。借助这个机遇,闽东地区开始发生了一系列异乎往古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闽东各县市出现了一大批因茶而兴的内陆市集、河港市集和沿海市集,如宁德九都、八都、外表、霍童、咸村、七步、萌源、上洋、贡川;福鼎沙埕、硖门、白琳、巽城、秦屿、点头、店下;霞浦的鸥港、牙城、盐田、东冲、柘阳;福安的苏堤、洪口、赛江、龟龄、社口、坦洋、上白石、穆阳;古田的水口、黄田、鹤塘、杉洋、凤都、大甲、平湖、七保;屏南的双溪、谢坑、棠口、忠洋、康里、漈头;寿宁的南阳、斜滩、平溪、南溪、下坪峰、桃洋、武曲,等等,这些新兴市集把散落在闽东各地的茶园和业茶的乡民汇聚起来,通过陆运、河运和海运交通网络把各地的茶叶和其他土货源源不断地向茶港三都澳或福州集中,再经三都澳和福州的商贸网络输往世界各地,原本联系有限的闽东各地以茶为媒逐渐演变为内在经济联系紧密的区域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以三都澳为枢纽,形成县城、乡镇、市集等多层次的市场网络,并与世界茶叶市场相连,初步具备了区域经济基本的内在结构,闽东这个原本相对闭塞的区域性世界遂一变而为茶叶外贸主导的,因而被深度卷入世界市场和全球体系之中的世界性区域,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随着福州、三都澳茶港的崛起,越海而来的西人、西事、西物、西制,以及各类新知新学,如洋商、传教士、洋货、商业管理、科学技术、近代教育、西医、慈善等亦开始“东渐”闽东,并影响闽东,闽东因此而成为“中国受西方工商业文明冲击较早、较直接、较全面和较彻底的区域”,在这个过程中,闽东这个传统农业区终于缓慢地踏上了近代转型之路。这一切都得益于闽东茶叶外贸的兴起与发展,可以说茶叶外贸是打开近代闽东区域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然而,现实却是,长期以来,由于学界对闽东茶叶外贸缺乏应有的重视,对闽东茶叶外贸的发展如何牵动区域社会变迁自然更乏人问津,这种状况应当改变。
四、个人的一点私心。闽东是我的故乡,我的青少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十八岁时才负笈他乡,采过茶,也种过茶,直到现在,我喝的最多、最喜欢的依然是来自故乡的茶叶,茶香四溢是我有关故乡的最深刻的记忆。每次品尝家乡的茗茶,就彷佛从舌尖上回到了故乡。近年来,每次返乡,各种变化触目可见,常常有一种“换了人间”之感,唯一不变的就是漫山遍野、伴着群山绵延起伏的青翠茶山,以及高山云雾茶弥散的缕缕清香。我知道,闽东成为茶乡的历史并不长,但我不了解闽东是如何成为茶乡的,更不了解茶叶是怎样改变闽东历史的,因此,每次返乡又总不免会生出一种负疚之感。近年来,地方学已成为一门显学,各地都在结合在地优势,学理与咨政并重,大治地方学。远的且不说,闽东北面邻居温州已集全市之力成立温州学联合会,大力推进温州学研究;南面泉州早在1991年就设立实体性的中国泉州学研究所,致力于泉州历史与现实的综合研究。相比较而言,闽东区域研究明显滞后,至今仍几乎是一片被学界遗忘的土地。作为一个从这片土地走出来且以史地研究为业的学人,自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走近闽东,关注闽东,研究闽东。
绍旭这本书是全面研究近代闽东茶叶外贸及其引发的区域社会变迁的第一部专著,书中以他多年辛苦搜寻和田野调查所得的海关档案、地方史志、清末民国与宁德相关的茶叶调查报告和茶叶专刊、茶商族谱,地契文书、茶人笔记、账本、茶票和茶商墓志铭、碑刻等资料为基础,并参酌前人和时贤的相关研究成果,首次系统地勾勒出1853 至 1949 年间闽东茶叶外贸起伏变迁曲线,并对这一曲线背后的复杂造因做了深度分析,进而多角度具体而微地展示出茶叶外贸如何牵动闽东区域开发和社会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茶叶贸易史和闽东区域史研究的一大缺憾。全书分上下篇,上篇在简要交代闽东地理环境、行政建制和乡土社会构造之后,聚焦闽东茶叶外贸在各个时期的变化,重点论述了闽海关时期和福海关时期闽东茶叶外贸的发展详情,以及随之而来的茶叶制作、茶叶运输、新兴集市、茶业组织、茶叶外贸管理等方面的适应性变迁,进而在与福建其他区域、东南沿海其他口岸,以及新兴茶叶外贸国的多重比较中揭示闽东茶叶外贸的特点;下篇则集中探讨近代闽东茶叶外贸与区域社会变迁的具体关系,并从区域开发、畲汉民族融合、女性地位的变化等三个方面详加论证。其中关于三都澳商业中心的形成,关于茶叶外贸如何促进畲汉民族在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关于茶叶外贸与性别分工,以及这种分工给女性地位带来的变化,等等,都依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做了生动的阐释,为中国茶叶贸易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个案。
当然,对绍旭而言,这部著作还只是一项初步的研究,可以延展和深化的地方还有不少,譬如闽东茶叶外贸存在哪些内在局限,茶叶外贸中洋商与本地茶商的关系如何,以及1949年以后闽东茶业和茶叶外贸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等问题,都需要做进一步的细化研究才能厘清。至于闽东区域开发,值得深挖的课题更多。希望绍旭再接再厉,在已取得的成绩基础上,继续立足闽东,研究闽东,服务闽东,为闽东研究书写新的华章。
本文系作者为孙绍旭著《近代宁德茶叶外贸与区域社会变迁研究(1853-1949)》一书所作序言,该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