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一座中型城市的市长选举很少能引起本地之外的广泛关注。然而,2025年4月举行的加州奥克兰市长选举却成了例外——不仅吸引了全国政治观察者的目光,还占据了《纽约时报》《Politico》等主流媒体的大幅版面。原因很简单:在经历了2024年大选的全线溃败之后,许多民主党人迫切渴望从任何可能的线索中辨识未来的方向。而一场发生在深蓝城市、围绕民生议题展开的地方选举,恰恰能够提供这种线索。
一
民主党人所期待的,并不是政党本身的胜利——就像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其他深蓝城市一样,奥克兰的大多数选举早已沦为民主党内部的竞争。自2018年,众议员奥卡西奥-科泰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常被简称为AOC)、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等进步派新星在初选中击败建制派政客、一战成名以来,党内竞逐往往都被塑造成“草根挑战者对阵体制既得利益者”的对决。这次的奥克兰市长选举也不例外。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2日,美国华盛顿,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奥卡西奥-科泰兹出席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听证会。
代表建制派出战的候选人是前联邦众议员芭芭拉·李(Barbara Lee)。作为该地区数十年来最具知名度的政治人物,李自1998年起就一直代表奥克兰所在选区担任国会议员,并与加州几乎所有重量级政要关系密切。她在宣布参选后,迅速获得了整个加州建制阵营的集体背书:前州长杰瑞·布朗(Jerry Brown)、民权组织“艾米丽名单”(EMILY’s List)、奥克兰市议会中七位议员中的八位,以及包括劳联产联(AFL-CIO)郡支部在内的所有主要工会组织,都相继表态支持。因此,自她于一月宣布参选以来,许多人便几乎预设了她将以压倒性优势胜出的结局。但接下来的三个月内,这一看似平稳的竞选进程却急转直下,演变为一场异常激烈的选战。
她的对手是前市议员劳伦·泰勒(Loren Taylor)——一位此前并不为外界熟知的政坛新人。泰勒出生于本地的非裔家庭,成长于奥克兰的公立学校体系,此前长期在生物工程与非营利机构领域担任工程师。在政治领域,他几乎没有竞选或担任公职的经验,与加州政界或民主党高层也毫无可依靠的关系,可谓这场选战中毫无悬念的“草根逆境者”。事实上,两年前他首次竞选奥克兰市长时,便不出意料地败给了一位获得建制派大力支持的对手。
二
在后奥巴马时代的大多数此类党内竞争中,建制派与“逆境者”的身份往往与意识形态密切绑定: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AOC、贾马尔·鲍曼(Jamaal Bowman)、科瑞·布什(Cori Bush)等一众“逆境者”新星,无一不是党内激进进步派的代表,而他们在初选中所挑战的,几乎清一色是立场更加温和的建制派人物。然而,劳伦·泰勒既没有AOC式的集会动员力,也缺乏那种充满民粹激情的演讲风格;他的政治主张更接近一位注重实用主义、政策效果与治理过程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而非意识形态斗士。相比之下,芭芭拉·李则是早在小布什时代就已声名远扬的进步派元老,即使在当今的民主党内部,她在国防、执法、毒品成瘾等议题上的立场仍属于激进一端。
与新泽西、弗吉尼亚、科罗拉多等浅蓝或摇摆州不同,在加州这样的深蓝州,民主党几乎在所有权力层级上都缺乏实质性竞争,而大量外部议题组织与活动人士却拥有显著话语权。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进步派早已主导党内领导层,摇身一变成为新的建制派。这也造成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局面:温和派候选人反倒成了必须挑战不利结构、对抗“不公平的党内机制”和“机器政治”(machine politics)的一方。
在此类选战中,逆境者向建制派提出的批评——如裙带关系盛行、阻碍大胆改革等——在建制派本身是进步派时,同样成立。奥克兰近年的局势正是这些问题的缩影:自上次选举之后,民主党建制派力挺的候选人陶盛(Sheng Thao)击败泰勒当选市长以来,这座城市便接连陷入经济困境、治安恶化与政治腐败等多重危机。

陶盛(Sheng Thao)
早在2020年,陶盛便是奥克兰市议会中最坚定支持“削减警察经费”(defund the police)运动的声音之一,曾多次公开主张将执法部门的预算转投至预防性社会项目,并投票支持削减警方预算1800万美元的法案。然而,随着疫情后的治安形势迅速恶化,她在随后的竞选中不得不对这一议题保持沉默。但在成功当选后,她迅速将此前的立场付诸实践:上任伊始即冻结本地执法部门的招聘。此举在治安本已紧张的背景下更显突出——作为一座人口超过40万的城市,奥克兰仅有约600名警员,远低于同等规模城市约1100人的全国平均水平。
陶盛还迅速升级了与奥克兰执法部门之间的对立。宣誓就职不到一个月,她便以“处理一项下属的内部调查不当”为由,解雇了警察局长勒罗恩·阿姆斯特朗(LeRonne Armstrong)。这一决定被广泛视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讨好其进步派基层支持者。事实上,一名退休法官已裁定阿姆斯特朗在该事件中的处理并无疏失;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是那种纵容警察暴力、抵制问责的右翼警界人物,反而长期致力于改革、提升执法透明度,并在奥克兰少数族裔社区中具有广泛的民望。然而,在解雇阿姆斯特朗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陶盛既未积极物色继任人选,也未填补警局的高层空缺,致使整个执法系统长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在缺乏领导、人力、资金和市府支持的多重压力下,奥克兰的警队难以有效履行职责,公共安全水平急剧下滑。而与所有“撤资警察”政策实践相似,最终受到最大冲击的,往往正是这些政策原本宣称要保护和服务的少数族裔社区。奥克兰治安恶化的趋势也在数据中一览无余:911紧急电话的平均响应时间居全加州之首,受害者等待警方支援往往长达数小时。2024年7月,一起加油站暴力抢劫案中,歹徒肆意作案40分钟,警方却耗时9小时才到达现场,造成损失高达10万美元。
在警局接获的暴力犯罪报案中,仅有6.5%取得了任何实质性的侦破进展。与此同时,陶盛领导下的市政府却无故错失了一笔高达1500万美元、原可用于打击有组织盗窃行为的州级拨款机会;911接线员的招聘工作也被搁置,尽管市府收到了超过1000份申请,却始终未予处理。
随着公共执法系统的失能,越来越多市民对奥克兰保障基本安全的能力彻底丧失信心。202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多达92%的中小企业主在遭遇盗窃或抢劫后选择不再报警。到了2024年夏天,奥克兰又爆发多起针对年长亚裔居民的抢劫与伤害事件,部分受害者甚至因担忧案件无人处理而放弃报警,进一步加剧了社区的不安与疏离。
安全危机的蔓延也迅速波及奥克兰的经济。除了大量中小商户因无法承受盗窃损失而倒闭,美国连锁巨头In-N-Out餐厅亦于2024年年中宣布关闭其奥克兰门店——这是该品牌历史上首次撤出某座城市。同时,奥克兰在2023年失去了其拥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职棒大联盟(MLB)球队“运动家”(Athletics),继NBA和NFL球队先后迁出后,使这座城市史无前例地不再拥有任何一支“四大联盟”球队。
更雪上加霜的是,陶盛在上任不久便陷入了极具可信度的腐败丑闻。自担任市议员以来,她多次利用职权延长并保护某本地公司与市政府之间的合同,推动有利于该公司地产投资的分区调整(zoning plan),作为交换,该公司所有者不仅为她提供了政治献金,她的丈夫更获得了一份无具体职责却待遇优渥的“挂名职位”。2024年6月,联邦调查局突袭搜查了陶盛的住所,并随即传唤了市长办公室的多份文件;半年后,联邦检察官在获得大陪审团批准后,正式以贿赂、电信欺诈和妨碍司法等多项罪名,对陶盛夫妇提起公诉。
这一丑闻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2024年11月,奥克兰市民以超过60%的支持率投票将陶盛罢免,彼时距离她的首个任期结束尚有两年多。为选出继任者以完成余下任期,市政府随即决定于2025年4月举行一次特别市长选举——也正是本文开头所提及,由芭芭拉·李与劳伦·泰勒展开角逐的这一场。
三
可以预见,陶盛作为一位由民主党建制派背书的进步派候选人,其执政留下的负面印象也不可避免地波及了同属阵营的芭芭拉·李。尽管李在历次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鲜少低于80%,这一次却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反对声浪,其中不少反对意见甚至来自她长期的支持者。这样的选民在奥克兰比比皆是。一位李的忠实选民对记者坦言:“我一直很感激她在国会中为本区发声,但此时此刻,我更渴望的是治理能力——让州、市能够正常运转。可自新冠以来,我越来越看不到我们这个党(民主党)有这种能力。”他将对民主党“找回治理能力”的最后希望寄托在了泰勒身上。

当地时间2025年4月15日,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长候选人芭芭拉·李在选举会上发表讲演。
事实上,许多奥克兰市民——尤其是来自工薪阶层与少数族裔社区的选民——都在表达类似情绪:他们一方面对李的国会生涯给予肯定与尊敬,另一方面却清楚地感受到,李所代表的那一套政治风格与领导方式,并不是当前奥克兰所迫切需要的。这几乎成为一种在街头巷尾不断被重复的主旋律。
李的竞选团队显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陶盛共享的“进步派建制”标签已成为巨大的政治负担。因此,她在竞选过程中刻意弱化自身以往的意识形态身份,转而将“团结”作为核心承诺,试图塑造一个能够跨越政治分歧、调和不同阶层与派系矛盾的领导者形象,而非过去那个始终为特定阵营据理力争的进步派代言人。同时,她将自己数十年的国会经历重新包装为一项优势,强调自己有能力为财政困窘的奥克兰争取联邦资源与拨款;面对陶盛执政留下的烂摊子,她也从未尝试辩护,而是承诺要为奥克兰带来“一个全新的开始”。
然而,许多选民对她的转向并不买账。他们认为,李所谓“争取联邦资源”的承诺空洞乏力,且现实上缺乏可行性——毕竟如今华盛顿的白宫和国会均掌握在共和党手中,她的从政资历反倒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负资产。此外,尽管李未公开为陶盛辩护,她却曾在2023年底反对罢免陶盛的投票中公开站队,这一举动也让不少选民心存芥蒂。更根本的是,许多人心中盘旋着同一个疑问:“既然过去两年建制派候选人已经让我们如此失望,我们凭什么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泰勒的竞选团队精准捕捉到了选民内心深处的挫败与倦怠,并将“执行力重于意识形态”作为竞选的核心理念。他借助自己在生物科技领域的多年工程师经历,以及成功运营扶贫非营利机构的管理背景,强调自己具备实质性提升市政治理能力的技术与经验。与李相对抽象的承诺相比,泰勒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可衡量的政策方案:他指出,加州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本问题在于开发程序繁琐,因而承诺推出一款“秒表”式工具,实时追踪市政审批流程;为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他主张要求市政雇员每周至少四天到岗办公;在公共安全方面,他则与陶盛划清界限,明确反对“削减警察经费”的做法,并回忆自己在与陶盛共同任职市议会期间,就曾多次在该议题上公开交锋。他承诺一旦当选,将优先恢复警力响应能力,并直言不讳地指出:“无法保障基本安全与秩序的进步主义,只是一场政治幻想。”
泰勒不仅在政策上与“进步建制派”分道扬镳,在价值层面上更是对“机器政治”进行了系统性批判。他指出,陶盛任内混乱、腐败横生,正是由于她的当选建立在强大利益集团与党内高层联手打造的选举机器之上,自然也就缺乏对选民而非“机器”的真正责任感;而芭芭拉·李同样身处这一体系之中,难以跳脱类似的逻辑。相比之下,泰勒两度挑战市长宝座,从无名小卒一步步获得广泛认可,完全依靠倾听选民、用清晰主张赢得信任;他强调,正因如此,他若成功当选,也必须依靠持续履约才能维护这种信任。他的政治视野亦不止于一场市级选举——在民主党因执迷于身份政治与意识形态“纯洁性”而失去大批选民之后,泰勒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参与重塑进步主义的方向:一个真正能赢回工薪阶层和少数族裔支持的进步主义,必须以切实改善他们生活质量为优先目标。
四
如前文所述,芭芭拉·李宣布参选时的初衷,原本是凭借自己在奥克兰数十年来积累的高知名度、进步派招牌与建制派支持优势,在选战中率先发力、无须激烈竞争便顺利当选。然而,泰勒不仅始终与她势均力敌,甚至在多个阶段的民调中略有领先,这一出人意料的局势也令全美政界观察者大感惊讶。

当地时间2025年4月15日,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长候选人劳伦·泰勒在东山购物中心为奥克兰市长特别选举投票。
为了提高选举的代表性,奥克兰市采用的是排序选择制(Ranked-choice voting),即选民按偏好顺序列出所有候选人,计票过程则分轮进行:每轮淘汰得票最少者,并将其选票依次转移给选民的下一个选择,直到某一位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支持。该制度的优点在于能确保胜者拥有多数支持,但结合加州的邮寄选票机制,也意味着计票过程往往旷日持久,长达数天乃至数周。
本次市长选举的计票持续了整整17天。选举当晚的出口民调、早期邮寄选票以及前几轮计票结果中,泰勒保持领先。然而,李凭借其建制派背景,更熟悉如何策略性运用这一制度:她在选战中与其他进步派候选人结成联盟,鼓励他们引导选民将李排为次选,同时不在选票上列出泰勒,从而在淘汰过程中让选票自然转移至李名下。这种投票安排也更容易被建制派选民掌握和执行。因此,在最终一轮统计中,李以53%的微弱优势实现逆转,成功当选。
尽管未能取胜,泰勒的表现对他的支持者而言仍是巨大鼓舞:他与一位在民主党内活跃数十年的政治老将不分上下,已足以证明,哪怕在一座以进步主义自豪的城市中,务实治理能力也正在成为日益具吸引力的政治主张。他的团队并未停止行动,仍在持续筹款、组织资源,着手准备2026年的正式市长选举——毕竟,这次胜出的芭芭拉·李,也仅是为完成陶盛未履行完的任期而当选。
这场选举所呈现出的意义,早已超越奥克兰乃至加州本身。它凸显了一个越来越难以忽视的事实:在短短数年间,进步派已迅速成为党内建制机器的一部分,而人们在后奥巴马时代初期对其“挑战体制、带来新气象”的印象,也亟需重新审视。更令人沮丧的是,奥克兰这几年的治理现实不仅证明,许多进步派未能兑现当年承诺铲除腐败、提升透明度、杜绝裙带关系等改革目标,反而在此基础上,又引入了另一类根本性问题——那就是他们时常过度执着于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而忽视了实际治理能力,最终将低效和失能也一并带入了原本就饱受诟病的“政治机器”之中。
事实上,奥克兰所反映出的政治动力,在过去几年里已越来越广泛地出现在全国范围。如今,民主党内部负责维持组织运作、筹款体系、候选人遴选与竞选战略的核心幕僚群体,几乎全部由受过高等教育、来自上中产背景的进步派人士主导。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在议程设定、候选人招募、选战走向等关键事务上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党内大多数有影响力的智库、论坛和民调机构也普遍倾向进步派立场,其发布的民调、政策备忘录、研究报告往往服务于强化该派别在党内的正当性与主导地位。此外,进步派吸引了大量富裕自由派选民支持,使其建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迅速成长为最有组织力的政治工具之一。这些PAC不仅在全国范围内筹款投放广告,还常常将“组织肌肉”用于攻击立场不一致的温和派议员,将他们在初选中挤出局,从而进一步压缩温和派在国会与地方议会的生存空间。在拜登政府的早期,第一任白宫幕僚长罗恩·克莱恩(Ron Klain)大幅左转其政策方向——从预算、基建到工会和气候议题,在国会进步派与温和派意见分歧时,他几乎始终偏向前者。这也为进步派输送了实质性的制度性资源。
早在2022年,来自佛罗里达的时任国会议员史蒂芬妮·墨菲(Stephanie Murphy)就曾在采访中警告,这种内部斗争和“党内纯洁性测试”将对民主党整体构成伤害。她的个人背景,本应是党内进步派最热衷讲述的故事——她的父母是越南难民,在她只有六个月大时举家来到美国;她本人也成为历史上第二位越南裔美国国会议员。然而,仅仅因为她在财政支出上持温和立场,并在“重建更好美国”(Build Back Better)法案上表示反对,她便遭到了进步派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定点广告攻击,最终决定不再参选,空出的席位随即被共和党人夺走。类似经历的温和派并不在少数:来自华盛顿州、拥有蓝领背景并在深红选区两度击败极右翼对手的玛丽·格伦森坎普·佩雷斯(Marie Gluesenkamp Perez),哪怕是民主党赢回众议院所不可或缺的人选,也因在学贷减免等问题上表达不同意见而多次受到来自全国进步派网络的围攻。同样,来自纽约的瑞奇·托瑞斯(Ritchie Torres)和宾州的约翰·费特尔曼(John Fetterman)——两位原本被视为进步派新星的政治人物——在就特定政策表达诚实批评后,也迅速成为组织化攻击的对象,有些甚至来自昔日盟友。
李与泰勒之间的较量,并非这种竞争模式首次在选举中上演。早在2020年,时任众议员乔·肯尼迪三世(Joe Kennedy III)便曾挑战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埃德·马尔基(Ed Markey)。肯尼迪年轻、充满激情、承诺带来变革,原本具备成为民主党重塑形象的理想代表。然而,由于他属于党内温和派,而马尔基则是参议院中最具进步派立场的议员之一,这场挑战最终反而让肯尼迪处于劣势。马尔基不仅没有因“左倾”失去建制派支持,反而获得了大量党内资源的倾斜,肯尼迪则未能获得进步派挑战者通常享有的关注与动员热情。结果,马尔基几乎不需与对手辩论,便轻松连任。这场初选,是进步派已在全国层面“建制化”的一个早期写照。
在一些深蓝城市,这一趋势甚至发展得更加迅猛。在纽约,真正掌控地方选举成败的政治机器,早已不是以如前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为代表的传统建制派,而是原本位于民主党边缘的激进左翼组织,例如工作家庭党(Working Families Party)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他们通过与教师工会、社区组织、进步派媒体以及党内领导人物的紧密协作,逐步主导了多个市议会和州议会选区的初选,直接将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推上前台。这也是为何AOC自出道以来,几乎不必面临真正竞争,便能屡屡轻松赢得初选。这种对地方机器的掌控,在今年的纽约市长初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进步派支持的候选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市议员苏文丹(Zohran Mamdani)。尽管此前毫无广泛知名度,进步派凭借其惊人的组织能力迅速集结资源,为他筹集了大量政治献金,争取到各级党内人物、名人、逾半市议员以及诸如卡车司机联盟(Teamsters)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等老牌工会的背书。
尽管进步派在纽约的执政成绩同样乏善可陈,温和派始终清楚,唯有推举具备高度知名度和显著政治资本的候选人,才有一线胜算,得以扭转局势、推进必要改革。正因如此,他们不得不将“建制性”作为首要考量,而非候选人的政策表现。在这种思路下,他们集体押注于“旧建制派”代表——希望借此作为自己政治复出机会的前州长科莫。
科莫的执政能力毋庸置疑。在他的领导下,纽约这个以住房成本高企、监管冗杂著称的州,完成了拉瓜迪亚机场等多个基建项目的翻新改造。然而,2021年迫使他辞职的丑闻仍为不少选民所诟病,成为难以摆脱的政治包袱。相比包括泰勒在内的新一代温和派政治人才,科莫的竞选策略显得明显过时。他依赖传统造势手段——深入非裔社区教堂、工会会堂与街区社区中心等地展开“零售式政治”(retail politics),但在社交媒体上的存在感微弱,错失了争取年轻选民与城市进步阶层的关键战场。而后者恰恰是新一代的政治机器所极其擅长的,从而为苏文丹提供充分的此类资源得以动用:在选战最后一个月,几乎所有具影响力的明星、网红与公众人物悉数表态支持苏文丹;与此同时,选举日当天突袭纽约的极端热浪则显著抑制了年长、收入偏低、以蓝领为主的温和派传统支持群体的投票率。在双重助力下,苏文丹在第一轮计票中便取得近10个百分点的领先,基本锁定了胜局(纽约采用与奥克兰相同的排序选择投票制)。
五
事实上,特别是在特朗普再次当选之后,已有不少观察者为这一趋势赋予了一个极其贴切的名称:“民主党的茶党时刻”。这一比喻在多个层面上都极为准确:茶党运动之所以能在共和党内崛起,正是源于该党在2008年奥巴马当选后的全面挫败,并借助基层选民对奥巴马政策的愤怒,将党内温和派逐出权力核心,最终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建制派。而这一过程最终催生了特朗普主义全面主导共和党的局面。

当地时间2025年5月20日,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芭芭拉·李在市政厅宣誓就任新市长。
对如今的“民主党版茶党时刻”可能引发类似后果,可以说值得民主党人保持高度警觉。首先,正如前文所述,许多进步派并未兑现其改革承诺——未能扩大党内人才通道、提升组织透明度,反倒形成新的排他性权力结构;更严重的是,其在执政能力上的表现也难以令人满意。陶盛治下的奥克兰并非孤例,芝加哥、洛杉矶、明尼阿波利斯等地的类似经验也提供了警示信号。至于纽约的苏文丹,其在公共安全、住房、经济和交通政策方面的立场甚至比陶盛更为激进,若其上台,势必将进一步加剧当地少数族裔蓝领群体的生活负担。更令人担忧的是进步派的战略重心。“茶党时刻”之所以能在共和党内赢得支持,是因为其集中攻击了选民对奥巴马政府最不满的议题,如救市政策与金融改革。而如今民主党内的“茶党派”,却将精力集中在移民、社会议题和意识形态争议等选民信任度最低的领域,几乎未能有效聚焦特朗普最具争议、最易击中的领域——如关税政策、经济民族主义与行政滥权。这种策略上的失衡,很可能让民主党错失重新赢回执政正当性的机会。
因此,奥克兰这场选举之所以意义深远,不在于它本身的结果,而在于它为观察民主党在这一关键十字路口上的角色与方向提供了一个真实而具代表性的缩影。李虽最终以进步派建制候选人的身份获胜,但她在选战中所作出的承诺——即向温和、务实的治理方向转变——是否真的能够在执政中兑现,仍是一个未知数。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温和派能否在2026年的正式选举中赢得更广泛的民意支持,重新获得党内的主导空间。而在纽约、新泽西等即将进入选举周期的地区,民主党精英又将做出何种选择?他们会否将意识形态纯度置于治理效能之上,最终使这些深蓝地区成为共和党在全国竞选中用以妖魔化民主党施政的“反面教材”?作为一个在历史性的失败后依然挣扎于寻找未来方向的政党,民主党在未来所需要回答的问题实在还有许多。
吉祥起名网 吉祥起名网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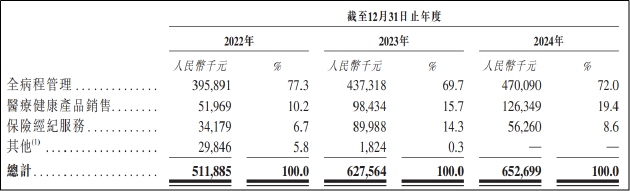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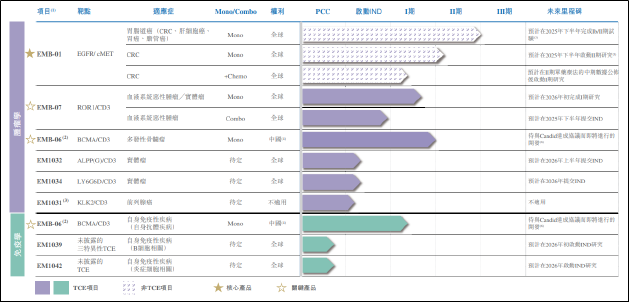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