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夏天,一系列新闻事件让“气候变化”这个话题变得特别具体。当这些极端天气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直接经验时,人们一方面开始直接关切灾难,另一方面也会感到不知所措。这种无力感和困惑,恰恰反映了个体在面对宏观气候危机时的普遍心态——既感受到了危机的切身影响,又对其复杂性和解决路径感到茫然。
然而,回避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气候变化已然变成了每个人日常的现实威胁。现有的气候事件报道往往局限于对灾难本身的描述,缺乏对其背后深层原因的分析。要真正理解当下的气候危机,我们需要超越表面现象,深入思考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的系统性问题。以下三本书,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提供了重新理解气候危机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
谁是最受苦的人?看见不可见的暴力与环境不平等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勃·尼克松(Rob Nixon)的《缓慢的暴力与穷人的环境主义》(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一书,是环境正义领域的经典著作。这本书引导我们看见那些在全球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的脆弱人群,是如何不成比例地承受着环境破坏的代价,成为气候变化中最受苦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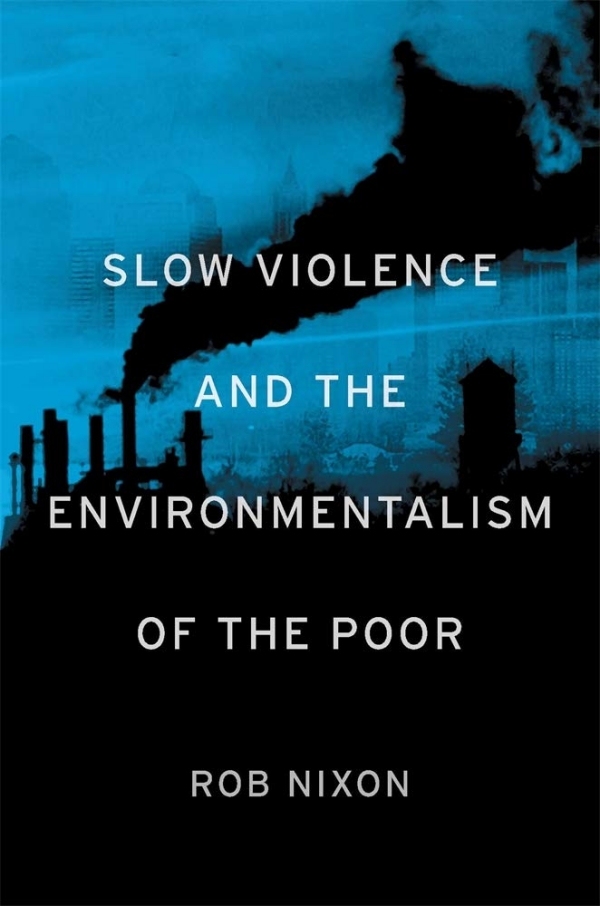
《缓慢的暴力与穷人的环境主义》,【美】罗勃·尼克松/著,哈佛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
尼克松用“缓慢的暴力”(Slow Violence)来描述那些“渐进的、脱离人们视野的暴力,一种延时性的破坏,其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分散的”。气候变化、化学污染、森林砍伐、冰川融化、战争遗留的放射性污染等,都是这种暴力的具体表现。它们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却因其过程的长期性、渐进性和因果链条的复杂性,往往缺乏戏剧性的瞬间和清晰可见的伤害,而难以转化为引人注目的新闻头条或激发公众情感的图像与叙事。这种“缓慢”的特质使其在公共议程中常常被边缘化,甚至被完全忽视。
那么谁是“缓慢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尼克松指出,正是全球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的贫困社群。他们生活在污染的土地上,使用被化学品污染的水源,呼吸工业废气,然而他们的苦难如同缓慢的暴力本身,都是“不可见的”。这种双重“不可见性”相互叠加,使问题愈发难以被看见和解决。
由此,尼克松引出“穷人的环境主义”,与主流“饱腹者”的环境主义不同,对前者而言,环境问题并非抽象议题,而是直接关乎食物、水源、健康乃至社群存续的生存问题。它不始于对远方荒野的浪漫想象,而源于最直接的生存威胁。尼日尔三角洲奥戈尼人(Ogoni)反抗壳牌公司石油开采,抗议的是被污染的农田和渔场;肯尼亚妇女发起“绿带运动”植树,是为解决水源流失和燃料短缺。这些行动本质上是环境运动,却因与生计、土地权、少数族裔权利等议题紧密交织,往往不被传统环境主义者所辨认。
面对难以被看见的暴力和被边缘化的抵抗,尼克松将希望寄予“作家-行动者”(Writer-Activist)。作家们能够凭借想象力和语言感染力,将无形、长期、抽象的威胁转化为可感知、具体、动人的故事,让不可见变得可见。肯·萨罗-维瓦(Ken Saro-Wiwa)为奥戈尼人的疾呼、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批判大型水坝,都成为连接被牺牲社群与更广阔世界的桥梁,推动了环境正义运动。
这本书提醒我们,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若不将被边缘化的声音置于中心,都将是片面的。它促使我们看见那些“远方的他者”——因我们的消费模式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因全球变暖而面临生存危机的岛国居民,并认识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的苦难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回归人的尺度:反思现代经济的增长逻辑与去人化的技术
环境正义的视角带领我们看到了气候危机下更加脆弱的社群,经济学家E.F.舒马赫(E.F. Schumacher)的《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 A Study of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则引导我们追问气候危机的成因。他将目光转向内在,探究我们信奉并习以为常的发展模式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就是问题的来源,并探索个体如何在一个异化的世界里重建有意义的生活。这本书的核心贡献在于,它为个体和小型组织提供了一套另类的发展哲学和实践工具——“中间技术”,以此来反抗劳动异化与人跟自然的疏离。

《小的是美好的》,【英】E.F.舒马赫/著 刘清山/译,四川人民出版社·后浪,2022年6月版
舒马赫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的两大支柱:永无止境的增长和追求巨型化的技术。他认为,现代经济学最致命错误,便是将我们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本”(如化石燃料、地球环境的容忍度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当作可以肆意挥霍的“收入”,并将这种挥霍颂扬为“增长”的成就。这种增长逻辑的形而上学根源在于,“我们对任何超越经济层面的价值缺乏信念”。为增长逻辑服务的现代技术也并非价值无涉,而是内嵌了特定的价值取向:追求巨型化、高速化和高度复杂化,以“取消人的因素”为内在逻辑。这种技术本质上是“暴力的”,因为它剥夺了劳动的尊严与乐趣,使劳动异化为换取工资的手段。
农业领域的问题更为典型。舒马赫强调,“‘农业活动’所牵涉的不仅仅是增加收入、降低成本而已,而是人与大自然之间的所有关系,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人的健康、快乐、和谐,以及其栖息地的美景。”然而现代专家的建议却是“工业化、抽去农业的人性因素;是集中;是专业;是只要能节省人力不惜任何物质”。当农业与工业的根本差异被忽视时,农业被改造为追求最大产出的“食品工厂”,土地、动植物和农民等生命都被简化为生产要素。这种做法漠视了农业的超经济价值,不仅导致环境破坏和农村文化崩溃,更造成人与自然、土地联系的断裂。
面对这种困境,舒马赫没有将希望完全寄托于宏大的系统性变革,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方案。他倡导的“中间技术”,是一种介于原始手工艺和发达国家高成本、高能耗技术之间的、真正回归到人的技术。它的目的不是最大化产量,而是最大化地激活人的潜能,让工作变得更有尊严和乐趣。中间技术具备三个核心特征:成本低廉,使更多人能拥有;适合小规模应用,易于分散化;相对节省劳力,但更重要的是解放人的创造性。
这一理念直接挑战了“大即是好”的主流发展迷思,为气候议题提供了与高端“绿色技术”或“生态现代化”不同的路径。后者试图用更复杂庞大的技术修复旧技术创伤,舒马赫则呼吁从根本上转变技术范式——发展无数小型的、地方化的、与生态系统和谐共存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小的是美好的》这本书相信,真正的改变是由无数个这样的“小”的实践汇集而成的。它并非号召我们退回到前工业时代,而是鼓励我们运用智慧,发展出一种更聪明的、更具可持续性的、能让我们的生活和劳动重归和谐的技术与生活方式。这种由内而外的改变,如同水面的涟漪,虽始于微小,却有潜力扩散至整个社会。
舒马赫于1966年创办了“中间技术发展小组”(Intermediat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Group),该组织现已更名为“实践行动”(Practical Action),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技术方案。
走向联合的变革:当下气候问题是否还可能由“危”转“机”?
舒马赫为我们提供了从个体层面出发的行动哲学,但当这些微小的涟漪希望汇成更大的浪潮时,我们往往会感受到系统的阻力。为什么即使很多人都想改变,整个系统却依然纹丝不动?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的《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则将分析的尺度从个体和哲学层面移开,走向宏观的政治经济学层面,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审视我们时代所遇到的气候危机,重新定义了气候变化的本质: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环境问题,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占主导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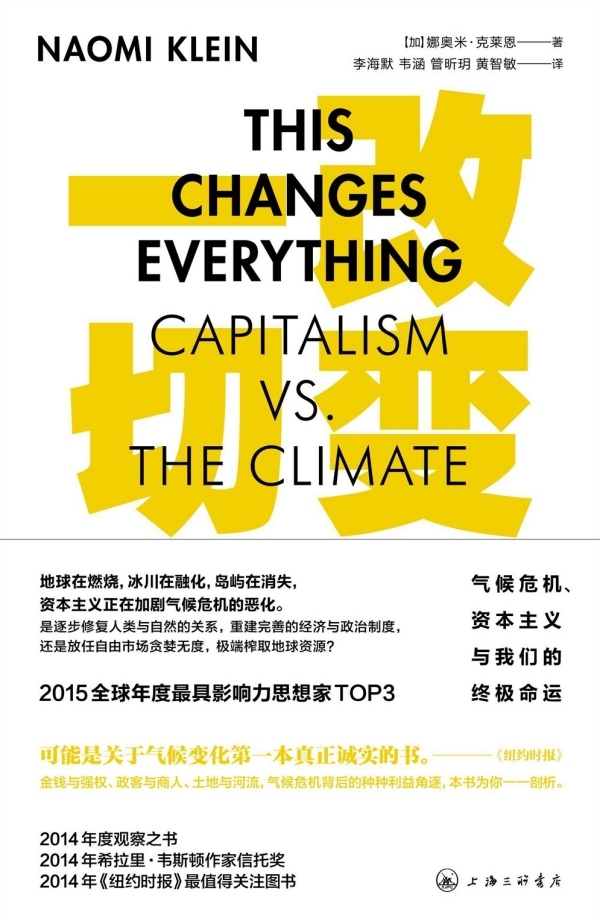
《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加】娜奥米·克莱恩/著 李海默、韦涵、管昕玥、黄智敏/译,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18年1月版
克莱恩认为,气候科学所揭示的物理现实,与过去四十年来主导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推崇私有化、去管制化和自由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气候危机要求我们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监管、重塑经济模式,而这些恰恰都是新自由主义所反对的。这解释了为何我们明明知道问题所在,却迟迟无法迈出真正有效的一步。我们一边承受着极端天气带来的后果,一边却在遵循着一套不断削弱我们集体应对能力的经济规则。
克莱恩进一步将问题追溯到“榨取主义”(extractivism)这一文化心态。这种将地球仅仅视为待开采资源的单向索取关系,源于殖民时代并在化石燃料的驱动下达到顶峰。煤炭和石油不仅为工业资本主义提供了动力,更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摆脱自然节律、掌控一切的幻觉。书中认为,气候变化本质上是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警钟,要求我们认识到人类并非地球的主宰,而是相互依存的生命系统的一部分。真正的气候行动不应仅停留于经济转型,而是应该进行一场世界观的变革,迫使我们从“榨取”转向“再生与照料”。
克莱恩不仅试图指出气候问题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她看到了气候危机中蕴含的巨大机遇。她认为,正是因为气候变化触及了我们经济系统的根基,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整合性框架,将各种看似分散的社会议题——就业、住房、公共服务、种族正义、性别平等等——团结在一起。当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而联合起来,反对高风险的开采项目时,他们不仅在进行环境抗争,也在争取更民主的决策权和更公平的资源分配。
因此,《改变一切》的视角是宏大的,它呼吁我们超越个人消费选择层面的努力,去参与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希望在于构建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联盟,共同挑战那个制造了多重危机的系统本身。
结语:从看见、行动到联合的可能
这三本书虽然写作时代和关注焦点不同,但为我们理解当前气候危机提供了互补的视角。尼克松的“缓慢的暴力”让我们看见了那些被忽视的受害者和他们的抵抗;舒马赫的“中间技术”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发展模式的哲学基础;克莱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则揭示了气候危机与社会正义的内在联系。
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个体确实容易感到渺小和无助。但正如这三本书所揭示的,气候危机同时也是一个机遇——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文明的基础,思考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构建一个更公正、更可持续的社会。这条从看见他者,到反思自我,再到联合行动的道路,或许正是我们在这个灾难日益成为日常的世界里,超越无力感,重建希望的真正所在。

